思想史 王泛森:从哲学史到思想史
导语:本文原题《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草稿》,曾刊于《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作为导读收入《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经出版方授权,本站转载。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台湾省中央研究院胡
本文原题《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草稿》,曾刊于《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作为导读收入《胡适英文中国思想史授课纲要遗稿》。经出版方授权,本站转载。原文有注释,此处删略。台湾省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收藏有胡适的《中国思想史英文大纲》。本大纲由1554个小笔记组成,是胡适1944年底至1945年在哈佛的教学大纲。这是他写《中国思想史》的最后一次尝试,但后来由于朱问题而黯然失色,这个问题开始得比较早,未能完成。这部《中国思想史大纲》与我们熟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很大不同。
一《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去哲学化”的变化,二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的一些观点的变化。我先说第一点。我在《国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胡适实际上在一个阶段受到了傅斯年的影响。1944年底到1945年,胡适在哈佛大学演讲,强调他讲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事实上,蒋永贞先生在《胡适》一书中的很多地方都提到,胡适并不想被称为哲学史家,而是想被称为思想史家。“哲学”原来是一个从西方来的词,日本也是从西方学来的。狭间直树有一篇论文,就是追索日本如何从欧洲学得到“哲学”这个概念。“哲学”到中国来跟王国维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其实近代的心理学、哲学、美学,这几种学问跟王国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从《王国维全集》中翻译的部分可以看到,王国维译过不少西方的人文着作。他写过四五篇与哲学相关的文章,主要是在说明,哲学这个东西对我们而言很陌生,但是个好东西。尤其在跟张之洞讨论到学制的时候,他一再强调,哲学是好事情,不要看它好像没有用,可它是一个重要的学科。蔡元培对哲学深感兴趣。他根据文德尔的课程写了一本《普通哲学》,早年翻译了《哲学要义》和《伦理学原理》。他翻译了保尔森的《伦理学原理》,后来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生中写评论最多的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蔡元培早年大力引进哲学,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般都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事实上,在胡适之前有两本书,一本是北大的讲义,即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另外一本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是同盟会的会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很多地方显然是针对谢无量。谢无量讲哲学,就是从伏羲、神农开始讲起,一路讲下来,胡适认为里面有很多过时的、过度信古的东西。其实谢无量所做的也是受日本影响、受近代西方哲学观念影响的哲学史,但是他不具有胡适那样怀疑批判的角度。胡适的书原叫《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印时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其实胡适在台北版的序言中已经明确表示,他已经放弃了哲学史的观念,改写了思想史,所以他不想要“第二卷”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为什么要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后来他甚至不愿意被称为“哲学家”。这种转折,因为涉及文字的部分多在私信、日记、未发表的演讲中,有些晦涩,没有那样吸引眼球。1922年,当胡适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四年后,哥大邀请他去当访问教授,他考虑到要写《哲学史》中、下卷而不去。可见他那时候还是非常投入哲学史的工作。到了1925年,他还出了一本《戴东原的哲学》。可是从1920年代末,可以感觉到胡适对于“哲学”的态度有了一个变化。傅斯年在1926年8月写给胡适一封长信,这封长信大概是因为字迹太草,所以没有被收进《胡适来往书信选》,可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面有。傅斯年对胡适说,你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着作,反倒是你的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着作。一方面哲学史的着作当时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人写了,但最重要的是你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人没有“哲学”这个东西,中国只有“方术”,任何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讲中国的思想,本身就是错的。傅斯年并说陈寅恪的看法与他是一致的,因为不能用伦理学、本体论、知识论去讲中国的东西。凡要用这些去讲,于古代的思想就有增减。傅斯年又对胡适说:“刚到英国时,我觉得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书。后来觉得听不懂德国哲学,觉得德国哲学只是德语的一些坏习惯。现在一个休谟偶然出现,我不知道所谓的。总之,我的大脑成了所有哲学的石头。我也对这一成就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当时知识界有慢慢疏远“哲学”的倾向。傅斯年在北大的许多著述原本都与哲学有关,但慢慢地在1926年和1927年,受当时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大概与逻辑实证主义有关,他开始疏远哲学。胡适在1926年回信给他,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这封信被收藏在历史和语言研究所的档案中,现已出版。当时胡适在巴黎。他说:“我和你最引以为豪的三样东西有些相似。1.最近每次用庞居士临终嘱托劝人:‘愿空事事如意,但小心别一无所有。’庞居士可能关注上半场,但我关注下半场。.....第二,捆绑人最有趣的是那些蜘蛛吐出自己的蜘蛛网。这几年,我努力学习,忘记自己。67年,我没有教西方哲学,没有读西方哲学书,一扫很多西方人的蜘蛛网。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为这一层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是哲学教授,不容易失去吃货。"可能受了这一影响,1927年5月胡适访欧回来以后,把他关于中古哲学文雅的标题定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此后他慢慢地就不再怎么谈哲学或哲学史,虽然也谈哲学的问题,但是他以后开课的名都是“思想史”了。1929年他在上海大同中学演讲《哲学的将来》,里面说了一些比较决绝的话。这份演讲稿并未发表,一直收藏在家人手上,直到编纂《胡适全集》时才收入。在这篇演讲中,胡适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最早乱谈性善性恶的孟子、荀子既可算作哲学家?”,“凡科学已解决的问题,都应承受科学的解决”,“凡科学认为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成为悬案”,“凡科学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应抛弃”。所以他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他说,“故哲学家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若不如此,但他们不是将来的思想家,只是过去的玄学鬼”,“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实验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他不用哲学史,而用思想史,因为“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关于胡适的大转变,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略作论述。除了傅斯年个人的影响外,还与时代思潮有关。用朱之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不去欧洲学习就没有发言权的时代。因此,西方知识界的最新动向往往会立即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的西方,质疑传统哲学甚至说“取消”是很常见的。胡适熟悉的杜威当然主张“重建哲学”,欧洲大陆也恰逢维也纳学派的聚集和出现。如《1870-1945年剑桥哲学史》中的“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终结”描述了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带来了哲学是形而上学和“哲学的终结”的思想。然而,像胡适一样,认为科学足以完全取代哲学的观点仍然是极端的。杜威认为,哲学和科学一样,是一种实验性的认知方法。维也纳学派认为哲学可以继续以逻辑和语义的形式发挥语言或概念分析的功能。换句话说,西方的说法普遍放弃了传统哲学中“知道终极真理”的信念,但仍然为哲学保持着卑微的地位。由于西方的最新发展,它往往是“真理”所在的地方。因此,胡适不禁对当时欧洲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压倒性气氛敏感起来。胡适的《哲学的将来》一文没有正式发表过,在他同一天的日记里,他把这个演讲的内容录进去了。其中就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等等。1929年他废弃《中国哲学史大纲》,改写《中古思想史长编》。商务印书馆在1931年将《中国哲学史大纲》收入《万有文库》的时候,胡适已将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并计划将来再重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这都是重要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主张废除哲学系、哲学和哲学的破产。钱穆的《师友杂记》中提到胡适是华北第一位西方哲学史教授,第一位西方哲学史教授竟然主张废除哲学系,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胡适教授西方哲学史多年,日记中记载他今天去找笛卡尔和霍布斯已经很多年了,但此时他主张废除哲学系。1934年至193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任,晚年接受采访时有这两个记忆。他说:“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系统。他贬得太低了,所以北大的课程叫中国思想史,不是中国哲学史。”因为胡适是文理学院的院长,他有课后发言的权利,课程名称都由他决定。".当然,不能说胡适从此与“哲学”分道扬镳,也不能说他不再提及“哲学”。但是,似乎有意无意之间就有这样的区别。“哲学史”和“思想史”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系统的,后者已经出现在历史中,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用“思想史”的角度与用“哲学史”的角度是迥然不同的。胡适说用“思想史”则可以写每一个时代,包括道士、佛教,包括他所最鄙夷的很多东西,但是它们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所以在《清代思想史》遗稿里,他说:“我们注重那代表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继承宋明传统的理学家。我们宁可取那编小说的吴敬梓与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讲理学的汤斌、张伯行。”我认为胡适从哲学史到思想史的转变,也代表了他整个学术观点的转变。此后,他一直接近史学和国学,但忽略了哲学和理论。他宣称我不是哲学史家,而是思想史家。有一段时间,他在为别人写作的时候,喜欢写朱的《宁为烦而不为微,宁为高而不为高,宁为浅而不为深,不为巧》,其实指的是历史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他在未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导言中,强调了用历史治理哲学的尝试:“因为我不满足于这种没有历史体系的哲学介绍,我想做一个具有历史性质的哲学介绍,所以我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是检验哲学介绍是否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做。”二
接着要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的转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从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的。这部论文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口试教授夏德显然意趣相反。夏德偏向孔教派,他给陈焕章那本《孔门理财学》写的序中对之颇为赞赏。《孔门理财学》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刚好是两个极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批判性的、疑古的;而《孔门理财学》是要发扬儒家的现代价值以及在财政方面的智慧的。夏德喜欢的是后者,不是前者。我们一直只注意到杜威,杜威看起来是对胡适的东西很欣赏的,他好几个地方提到,写完以后交给杜威看,杜威也表示赞许。可是夏德喜欢《孔门理财学》这样的东西,所以他跟杜威的看法显然不同。蔡元培在开篇就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了一篇非常果断的序言,并提到它有四个关键点:“证明的方法”、“简明的手段”、“平等的视野”和“系统的研究”。其中,在“言简意赅”中,他提到“切断大众流,从老子的孔子开始”是非常重要的,意思是从老子开始,而不是从伏羲或尧、舜、禹、唐开始谈论中国哲学。胡适的哲学史以史料批判为中心。他深受当时康乃尔大学西方哲学史老师Ku·莱顿的影响。西方哲学史的老师非常重视史料、时代背景和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认为没有这些东西,写哲学史是不靠谱的。因此,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大家都注意到了杜威的影响,却忽略了德莱顿的影响。其实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深受欧洲理想主义传统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列出了他写这本书时所指的西方。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德尔的阶级,他也深受文德尔阶级所写的西方哲学史的影响。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当时看来:一是用西方哲学史或哲学史的概念系统梳理古代哲学。其次,他对史料的批评具有很强的疑古精神。他想重现学校的制度、教学和起源。他批判旧书文风不清,还原各种理论的真相。不可能“搞乱教义的秩序和学校的传承制度”。《管子》既不是真正的书,也不能作为关中时代的哲学史料。这些东西在谢无量的书中找不到。在谢无量的书中,“烟斗”当然代表烟斗。胡适认为史料应该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有一个鲜明的主轴,即进化论。譬如他写庄子的时候提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认为这个就是“生物进化论”。当时有人批评马叙伦抄袭胡适这个说法,但马叙伦认为自己是师承章太炎的看法,这在当时的《北大日刊》是一桩公案。后来胡适在台北版的序言里面讲,他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庄子没有生物进化的看法,那是当时他作为年轻人一个大胆的说法而已。前面提到过,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深受枯雷顿影响,枯雷顿写西洋哲学史时,非常重视进化论在近代西方哲学上的作用,所以胡适在这本书里面讨论先秦诸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共同主题就是生物进化或者进化的思想。他讨论到墨子,讨论到荀子,讨论到其他许多,这都是他其中一个核心的观念。任何学说都是一个发生学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不变的东西,它有个过程,一个发生学的过程。胡适认为“对东周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只能抱有怀疑的态度”,所以要盲目相信古籍。先秦诸子无一可靠。“大约89%的庄子是假的,“韩非所作所为”只有10/2可靠。”《左传》不可信。《尚书》能否作为史料很难决定...无论如何,历史数据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一本古书《诗经》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史料。这是一本1980年出版的书。他当时的观点是,东周以前的古籍很值得怀疑,《尚书》、《左传》不能作为史料,所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对社会背景的描述变得很少,很多都引用了《诗经》中一些关于当时战争和人们流离失所的话。但在1944年的《中国思想史大纲》中,他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然而,人们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一变化,因为他们没有清楚地了解他后来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看法。其实从其他痕迹和其他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但并没有这么系统的展示出来。这个大纲特别谈到“遗传方法”,认为一个理论有两个目的,是一个发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不谈古代的经书。真相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所以对爷爷奶奶和孙子孙女来说都是一种方法。《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另外一个特色是西洋哲学的参证。《先秦名学史》是用英文写的,现在也有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的序就讲得非常清楚,他有很重要的现实关怀,要用西洋哲学里面的逻辑学方法来复活中国先秦诸子里面的逻辑思想,用很有逻辑的思想来改造这个民族没有逻辑思维的习惯。所以胡适是非常清楚地要用西方的逻辑学来检讨中国先秦的名学思想,他的这本书里面用了很多西方的哲学,用得比较多的比如斯宾塞、康德。他这时认为东西哲学可以互相印证、互相发明,是因为人类官能心理大概相同,如认为《老子》是西方的“自然法”,认为先秦诸子各家皆有生物进化论。直到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很多人问他为什么没有读完《中国哲学大纲》中、二卷。问他的人一定不知道胡适的观点变了。其实他现在要写的是《中国思想史》,整个《中国思想史》,从胡适留下的《大纲》来看,他的《中国思想史》的概念和《中国哲学大纲》是不一样的。在1945年英文版的《中国思想史大纲》中,他一开始谈到中国古代的思想跟希腊、罗马、欧洲等等的比较的时候,就提出,“为什么我讲的是history of thought,而不是history of philosophy”?他的言词里似乎表示,如果要写哲学史就得讲在西方哲学标准下能成系统的、抽象的知识论、本体论那样的东西。可是,他写完先秦那部分接着要写下去就不行了,接下去很多都是宗教的,佛教、道教的或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在严格意义上,至少在胡适看起来,并不是“哲学”。我认为这个大纲有几个特点。与《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比,一部是1919年,一部是1944年。25年过去了,很多人对胡适的看法都变了。这里我举几个例子:首先,胡适对史料的批判态度没有太大变化,但也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起源非常悠久,他非常重视时宇研究所当时在殷墟进行的15次发掘。我认为这15次发掘改变了他对许多古代事物的看法。因此,他非常重视傅斯年的《易夏冬解说》、董作宾的研究以及古代东西方集团的说法。事实上,他用这个背景来重新谈论中国古代的思想。他还谈到了很多可以和思想相关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是在孔子或者老子之前的,不像《中国哲学大纲》认为一切只能从老子开始。由于胡适的关注点逐渐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他非常重视思想史意义在古代考古发掘中的影响。这使他能够从商朝的宗教、人类的殉难等方面讲述中国的思想。
前面提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但在《中国思想史大纲》中,胡适费了许多笔墨讲老子以前的思想概况。他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一定非常古,不像以前那样宣称,“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他也引用了很多《左传》《尚书》中的材料,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则认为《左传》跟《尚书》不可信。所以这种看法已经变了。他比较愿意承认,在考古的证实之下,很多东西都可以信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先秦诸子的起源的问题。《中国哲学史大纲》否定诸子出于王官说,而又不信《尚书》《左传》等书,所以对于先秦诸子之兴起,依《淮南子》说是起于“救世”。而《中国思想史大纲》则颇讲述先秦诸子的宗教与思想背景,但仍未见提到诸子出于王官之论。当然,这本1554页的《大纲》吸收了他过去几十年对思想史的研究观点。然而,有些观点并没有改变。比如他对佛道做了大量的研究,却极度愤世嫉俗。他非常重视中世纪所谓的“印度运动”。胡适在哈佛大学300年时,应邀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中世纪“独立运动”的文章。即使是现在,我还是觉得那篇文章很有见地,很有价值。它讲述了中国人整个世界观、时间观、人生观等的重要变化。在这篇论文中,他还做了许多比较,这是以前没有的。佛教从此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反映。对理学,他当然还是持比较批判的态度。他跟陈寅恪不一样,陈寅恪认为宋朝的思想学术是最光辉、最高明的时代,可是胡适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也用美国人所比较了解的词语,譬如讲东周时,他用东罗马帝国来比喻;讲宋代的“新政”、支持“新政”的人时,又跟罗斯福的New Deal联系起来。总之,他用了很多当时西方人比较熟悉的词来讲。像讲孔子以前是《旧约》、孔子以后是《新约》的时代等等;我们把理学译成Neo-Confucianism,他不是,他译成Rational Philosophy。不过他讲道学的几个新派时,似乎讲得太无为、太消极。如他认为邵雍、周敦颐都是道家思想家。当然他一直讲到清朝,讲到颜元、李塨就结束了。我几年前看了梅光迪的文集,看到他们的通信,才知道原来早期胡适是非常赞赏程朱理学而反对颜元的,而梅光迪在当时则反对程朱理学并且是支持颜元的。后来这两个人在新文化运动里面成为最激烈的敌人,而且他们的思想刚好倒过来。但另一方面,胡适的学术态度仍然是一贯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根据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程度,对东周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只能有怀疑的态度”;还是他在《古史辨》第一卷《自报古史读本》中说的:“现在把古史缩短23000年,从《三百首诗》开始。未来,当金石学和考古学在科学轨道上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利用土地下发掘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代史。”。言下之意,如果考古发现充分,他未必不能回心转意,《中国思想史纲要》引用了大量关于北京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考古资料。,这也说明这是胡适的一贯态度。但由于考古中没有夏朝文物,《中国思想史大纲》中也没有提到夏朝。同时,由于商代丰富的考古发现,他写下了商代的许多部分。从前面的讨论来看,胡适在五四之后的二十几年里面有了重大的变化,它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对哲学的态度,一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重估。过去,有人认为胡适没有把哲学史中卷写下去是因为后来被佛教卡住了,没办法像处理先秦诸子那么得心应手。可是现在发现还有一层原因,因为他整个看法已经变了,他已经不再继续写哲学史,而是要写思想史了。当然,还有人困惑,胡适是哲学系毕业的,可他好像变成了汉学家一样,尽管这么多人一再呼吁他:你没有在哲学和思想上作一个大的对抗,使得左派的思想如此蔓延。胡适最后在离开大陆之前,在北平作了一个《水经注》版本的展览。当然也有一些人非常反对,可还是有一批人津津乐道。胡适最初是用西方哲学的标准和规范来谈论先秦诸子的,所以他的出发点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反复说明:“我用的比较参考资料是西方哲学。”但是,东西方哲学的相互印证和发明,并不意味着我们也有西方的东西,而是孕育和发展了民族的光辉,夸耀了我们自己的思想。然而,最终他还是希望东西方哲学能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知道50年后还是100年后会不会有世界哲学。”。人们认为有一种普遍的哲学措辞,它不同于那些持“思想史”观点的人。从“哲学史”到“思想史”,呈现出从普遍到更加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趋势。不仅有几个重要阶段符合“哲学史”的定义,而且每个时代的思想都值得书写。他说梁漱溟、梁启超所讲的正统哲学,800年前才存在,后来就消失了,好像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代表这些思想了。此后的现实变化是,胡适慢慢疏离了中国哲学圈。其实从《胡适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国哲学会、《哲学评论》创始的时候,他都是参与筹划的人,但后来,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到美国去,他就不在哲学圈里活动,而变成史学、汉学圈里面的人了。当时有人认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转向考证,异化了哲学和思想的大问题,这是他们无法反抗左翼思想的原因之一。比如傅斯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后,他在一些小本子上写下了这种自省。这种内省可能与胡适逐渐疏离哲学有关。胡适是当时学术界的核心人物,但他的关心却有着不同的地方。冯友兰、贺麟、黄子桐等人逐渐成为这个哲学圈的中心。当时,哲学会和哲学评论是另一群人。我认为两个圈子逐渐分离是1930年以后的现象。何霖在《文化与生活》中提到,1930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想谈哲学、谈价值、谈现实生活的人的圈子,但学术界又出现了另一种非个人化的倾向。当然,他指的是哲学圈的人。即使在哲学阵营中,冯友兰也不同于其他传统哲学家。任说:“比如冯老师讲课,一定要讲清楚。但是,中国哲学中有一个直观的东西,是可以用言语理解的,这个部分也是核心部分。...但冯先生不承认这一点。”这使得冯重新分析却没有认识到,包括《贞元六书》中的理学思想在内,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这使得他与其他人,尤其是与理学哲学思想仍有一定的距离。结论在以上这一篇短文中,我主要透过胡适后期在哈佛大学讲课的一份英文大纲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胡适中年以后疏离“哲学”,并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的过程。这个转变,对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甚至宣布想废除北大哲学系,同时也使得他与这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而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透过比较,爬梳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到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这25年间,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免责申明:以上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不代表远东新闻网立场!登载此文只为提供信息参考,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目的。如有侵权或内容不符,请联系我们处理,谢谢合作!
当前文章地址:https://www.ydj6688.com/caijing/439565.html 感谢你把文章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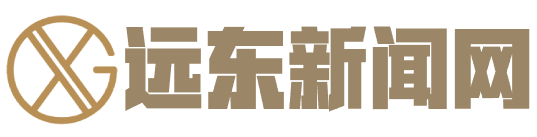
 财经新闻
财经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