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 台湾女作家胡晴舫:小说家的职责是什么
胡,作家,生于台北,现居北京、上海、东京、纽约、巴黎等城市。他的作品触及了全球文化现象。他出版的作品有《旅行者》、《机械时代》、《城市的忧郁》、《我的一代》等。其中,《第三人》获得第37届金鼎图书文学奖。2019年6月,《群岛》出版,描绘了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众生悲欢,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和孤立的处境
“不把它拉开,你就看不到全貌。”
曾经,我以为胡很小。她出生在台湾省,27岁写了第一本书,在过去的20年里出版了12本书,但只有三本书在mainland China出版。它引起了一些关注,但也非常有限。豆瓣上看过的人数不超过1000。
直到两年前,看到香港铜锣湾诚品书店重印的一批新书,我才意识到,她可能比我想象的要关心得多。去年,她作为嘉宾出现在香港书展上,与马家辉同台对谈,“默默无闻又低俗?——我处在互联网时代。”谈话结束后,我去找那个被人群遮住的骨瘦如柴的女作家,表示愿意采访,却忘了带名片。
到家后,我通过脸书联系了她,确定了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当时不知道社交账号不是她管理的。面试结束后,她给了我一个私人gmail邮箱,第一次沟通成功。就像4G时代的两位老太太,我们在电脑屏幕前如释重负。“好邮件,联系很强。:)”她在邮件中说。
那次面试,她让我住在香港大学附近的西餐厅科博之家,人均消费近400元人民币。餐厅由K11创始人郑志刚设计,负责的面点师两次被评为亚洲最佳。
点菜时,她用英语,我用粤语。她的粤语越来越差。早年在香港,她不会说话,但能听懂。语言障碍,所以我们必须加强视力。即使她住在日本和法国,她仍然依靠观察她的话。“我喜欢看人和预测对方,所以我必须看着他的眼睛看得很紧。我发现我能读懂很多情绪,有时候对方会有点惊讶,以为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面试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我就像被女巫盯着的水晶球。虽然不时有笑声,但大部分时间都笼罩在一种严肃整洁的气氛中,带着软糯的台湾省口音。
胡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受访者。她表达得很清楚,一旦发现不够准确,就会加上“应该这么说”来纠正自己,但同时也无形中要求你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参与其中。如果我们手边有黑板,她可能会敲着说“我刚才强调了”、“你要记住”、“再来一遍”。她明白细节的重要性,但这种意识似乎和她的警惕一样强烈。如果你不问,她就不会开口。
我对此深有体会。光看她的书名,大概就能领略到作家的气质——中性、隐秘、自由。她相信格雷厄姆·格林所说的,一个成功的作家应该是城市里的一个臭虫,而不是吸引任何注意力。“像某某进来了,人家都知道她是某某,人就要拿出最好的一面。但是当他不了解胡的时候,他会向我展示真实的一面。作家要做的就是看到人性和他最自然的状态,然后把那个东西写下来。这是我个人的信念。”
她回忆起当时课堂上有蛋糕,孩子们蜂拥而至,只有她呆在原地的场景,就像普鲁斯特在宴会上礼貌而安静地站在一旁拿着酒看着一样。“只有站在边缘,才能看清社会的主体。这也可能是作家的宿命。从小到大,你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你在现场,但没有融入其中。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拉开,你就看不到全貌。”
1995年,25岁的胡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完成戏剧硕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省,在《时尚先生》国际中文版工作。后来花花公子邀请她加入。“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说你敢给女人编辑,我就试试。”
她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孩子,循规蹈矩,孤僻。她上小学三年级,在家翻《红楼梦》《乱世佳人》等著名故事。她没有玩伴,不与外界接触。当她成年后,她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成为她选择工作的最大诱因。
在《花花公子》期间,她采访了才真旺姆、马英九和陈水扁,接触了黑社会、电影界等各种人士。“看到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金钱关系、情色关系,我觉得对我很好。”
一年后,他辞职了,因为他觉得不再有趣了。1999年,她正式移居香港。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作为《南华早报》的商务代表,她频繁前往内地寻求合作机会,在上海、香港、台北或北京忙碌了一周。带着很多疑问,就像亨利·詹姆斯描述的在伦敦的美国人一样,她观察了生活在上海的台湾省人和城市本身——这些空闻起来怎么样,水尝起来怎么样,人们说话的口音,以及他们每天关心的事情。关注跨地域写作主题。
2005年,她辞职开始全职写作,并在近十种期刊上发表专栏文章。她在香港待了四年,2009年和2013年分别在东京和纽约生活,2016年6月底再次回到香港。
胡和
网络时代的孤独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还想回香港?
胡:我的父母在台北。我喜欢住在亚洲。我对香港有一种依恋,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纽约和香港反差巨大,你真的很想回来?
胡:毕竟我是中国作家。长期面对外国作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让我觉得我比他矮一点。然后我们中国的读者经常让我觉得中国作家不够好,别人是世界文学。
人物周刊:你在纽约收到过这样直接的评论吗?
胡:我觉得很明显。每个人都崇拜它。比如当时有人想找个作家跟外国小说家谈,然后问我要不要去,因为我住在纽约,但是对方的经纪人根本不理你,说你先看看简历,看能不能跟他谈够。我觉得非常...
人物周刊:但可能是因为他不认识你,所以他需要…
胡:如果我不知道谁是谁,我会悄悄去谷歌找书。我不会告诉他。请把你的简历给我,这太粗鲁了。问题是,每个人都会觉得正常——欧美作家比我们领先一步。
人物周刊:做了文化交流工作后,你的影响力会比当作家时更大吗?
胡:当然不是。我觉得文学影响最大。但是,我一直说,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人们去做,所以我会去蔡明亮唱歌,去林强谱曲。我想用我的作品告诉大家,请不要妄自菲薄。其实我们亚洲社会也有非常实验性的文化产品。没有人比任何人更好,每个人都可以很好。当然,我的挑战是以前只有一个人写,现在要接触人情。我很少出版自己的书,但我现在想推广这些艺术家。好在都很优秀,不用我说太多。
人物周刊:接受一批采访会不会让你不习惯?
胡:当然,我不会习惯的。我学过戏剧,所以知道是角色扮演。我只是一个推广文化的角色,但对我来说更舒服。因为人们在谈论自己的作品时都是比较害羞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写完书就从来不回头看,生怕看了会觉得丢脸,写作也会继续往前跑。我想我还没有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如果我写《纯真博物馆》,我会很开心。
人物周刊:但是他们必然会关注你的写作。
胡:是的,但是如果你读了我的作品,你就会知道我有一本书叫《施虐者》,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的成长的。写的时候,我二十多岁。刚开始的时候,我要探索自己是谁,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当时我很悲观。我以为其实社会想让你成为一个正常人。只要你每天头发干净,身体没有异味,穿衣服,进地铁就要付钱。如果你打了人,你会说对不起并交税,他们会不理你。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极大的自由。从那以后直到我写《匿名》,我一直对匿名这件事感兴趣。当你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你可以在街上自由自在,但是当你在刘德华的时候,你压力很大。当然,我不是说默默无闻一定是好事,而是比较中有得有失。
人物周刊:有哪些与读者沟通的渠道?
胡:我的出版社告诉我,我自己都不敢问。
人物周刊:你怕什么?
胡:恐怕他们说了什么我就写不出来了。我基本上认为应该这样说。我真的相信“作者已死”的理论。写作基本上是两个人做的,一个写,一个读。我个人觉得,读不读由读者决定。我不敢也不应该照顾它。阅读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阅读可能感觉还行,也可能感觉不好。我不应该控制它。是另一个主体的生命体验。如果成为他的人生经历之一,那将是我的荣幸,我很开心。
我的读者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也很安静。比如我的脸书是出版社经营的,没有人喜欢,也没有人透露一些私人想法。每次他们帮我发布一些信息——她出现在这里,她就出版一本书...与一些作者不同,她与读者互动。
但是每出版一本书,就会很快卖出去,卖出去。其实我的销量也不是很小,不主流的原因是我不怎么出来,我离台湾省的文坛很远,在mainland China出书也没有宣传,但是你居然找到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阅读行为,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一个读者,所有我喜欢的都是自己发现的。我觉得那是我的作者,所以我的忠诚度很强。我想我的读者可能和我有同样的性格,就是相当独立。
人物周刊:没想过开微博?
胡:不,你认为我应该驾驶它吗?
人物周刊:你在书展上讲了《网络时代的我》,你不想参加吗?
胡:我参加了推特和的活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开微博,当然要观察,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这是我们的时代。即使不去微博,也一定会受到微博的影响。
人物周刊:你会看吗?
胡:没有,其实这件事我不是抗拒,但是我很清楚我是无法控制的。我有时看一些网上名人。我钦佩他们的勇气。我认为这不容易。我觉得公众真的是大海。他可以把你捧到顶峰,也可以毁掉你。自媒体运营是一项专业技能。因为我意识到这很重要,所以我不容易做到。我和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件事,因为媒体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不说话,各说各的话,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时代。如何恢复公开对话空,这个平台在哪里可以听到对方?
人物周刊:互联网出现之前的空时期是否完整?
胡:当然不是。过去话语权被垄断,谁能进谁能出的大门被控制。网络的好处是敲掉了门和高墙。过去有门的时候,虽然有警卫,但能听到一些不是朋友的话。像以前的报纸一样,它很平。报纸上有10条新闻,也许只有一条。这是我关心的,但我会针对其他9个标题;但现在真的不是了。我找了一样东西就走了,但是旁边什么也没看到。脸书更可怕,因为它认为你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它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推给你。因为我在柏林收集公寓,它一直把柏林的信息推给我,我忘了还有法兰克福。人们有诉说的欲望,因为他们想被听到。他们不能告诉自己。媒体也是如此。
人物周刊:网络时代人会越来越孤独吗?
胡:有一点,我现在有一个粗浅的看法。我觉得过去的人好像觉得孤独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状态。现在孤独似乎成了一件悲哀的事情,尤其是看到大家在网上幸福地生活着,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痛苦?
人物周刊:你自己注意到这种孤独了吗?
胡:我很好。我真的不怕,因为我从小就不受欢迎。但是以前人不吃香的时候会有时间差距,联系不到你的原因有很多。现在没有理由了,有手机,有WhatsApp,有朋友圈,看到你所有的朋友都在吃饭,就在离你办公室50米的地方,奇怪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我问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会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自信,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如果我爱你,喜欢你,吃饭的时候就会想起你。
人物周刊: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不自信和不自信的感觉?
胡:我应该有。这就是我开始写作的原因。我想任何一个开始写作的孩子,都是有点心不在焉的。
2019年的新书《群岛》描绘了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众生悲欢,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和孤立的处境
人们很难原谅,至少很难理解,这是作家的宿命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胡:小时候经常被送去写作,大学的时候在外语系学习。我和文学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但是因为喜欢读书,小学三年级就看完了《红楼梦》,真的知道自己的文笔不是很好。后来,我开始出版,因为我意识到我面对的时代与以前不同了。前者流动可能是因为战争和饥荒,但我这一代在台湾省的孩子相对幸福。他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战争,也没有巨大的灾难。我们因为学习和工作而搬家。我很好奇北京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去了北京生活,表明我们真的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每个作家能做的就是诚实地写下他看到的世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作,知道我可以谈论这些事情。
人物周刊:你不觉得在台湾省逗留期间有什么值得写下来的吗?
胡清玄:写家庭,人也在写家庭;写童年,人们也写童年。虽然我喜欢写小事,但我喜欢在小事中看到大时代。如果有人写得比我好,我不需要写。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相信,在我决定发言之前,必须由我来说。我仍然有这种自信。我明白我站在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在台湾省长大,很小的时候就来了香港。我住在北京和上海,我是20年前做这件事的,不是现在。我也碰巧在美国和欧洲有经验。我相信我是时代的产物,我必须把这写下来。
现在,我为什么对互联网感兴趣?因为互联网是人们心灵的展厅,我不认为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我在观察它。
人物周刊:会有真相,不是吗?
胡:我觉得很少见。当一个人有了自媒体,如何表达自己是小说家必须观察的。即使是普通人也知道角色扮演。
人物周刊:你说你的文章很少用“我”,因为你觉得作家很少真诚地出现。
胡: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直到《柏林的童年》一书才使用“我”。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大家写的提醒有关系。我一直希望自己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不要太放纵自己。我的问题不一定是读者的问题。
人物周刊:哪些作家或作品激发了这种自我提醒?
胡: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台湾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强调情感写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抒情传统,对此我有一种本能的抗拒;第二,因为读的是外语系,当然也受到学的其他语言的影响。第三个原因是,女权主义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非常流行,我一直被我只能写自己的身体,我的成长经历和痛苦所限制,我不想被这件事所限制。
作为一个作家,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野心,那就是要创造胡的声音,这可以不分性别,无所谓,但重点是它必须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等了很久。直到27岁,我才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旅行者》。我不想模仿任何人。当然很多人对我有影响,但我不认为模仿村上春树是出路。我在等自己的声音出来,现在想破,因为胡的风格太明显了。
人物周刊:“过客”就是你在路上实际遇到的所有人?
胡:是的,你也注意到了,很难界定是散文、议论文还是小说,因为里面有小说的场景。
人物周刊:你到了《办公室和她》就开始写小说了吗?
胡:“办公室”是虚构的,“她”是半虚构的,也不是虚构的。应该说是有加工的,两个人的原型放在一起。我的原则是不直接写我认识的人。小说家必须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我看到一些社会现象,然后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但如果直接写,其实记者已经可以做了。我还是觉得,如果编不出来,就不是小说家。其次,我觉得直接写我认识的人是不道德的,所以谁想做我的朋友,也就是你把心里话告诉我我就告诉你,其实是一种背叛。
也可能是我在无意识地抵制台湾省的主流私小说。我觉得私人小说只能偶尔做,之所以会出来,是因为写的人不知道会被看到,只是写给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看。正式出版私人小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违背了写作的初衷。我还是想强调,小说是小说家最好的东西,它让假的变成真的,让真的变成假的,但你可以通过那段旅程了解真相。
人物周刊:写了《旅行家》之后,坚定地觉得自己想当作家?
胡:是的。我觉得女性是作家,肯定是工作,我很重视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家人总是认为我写作。这是一件事。我觉得这个很难,但其实比你想象的要难。
人物周刊:大家都很尊重张爱玲,觉得她很厉害。
胡:是的,但是我觉得在现实中,没有人会去挑战罗怡君留在家里,但是很多人经常认为我每天在家里无事可做。他们不知道我每天都要看书查资料,然后生产东西。他们会认为男人是知识分子,女人只是写好玩的。
我可能是女权主义者,我编了《花花公子》后就是这样。人生一定要经历一些后知后觉才知道,当你和那些人物打交道时,他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即使一个恶人,他的动机可能是最善良的,但他最后的行为是一件邪恶的事情,你仍然要批评这种邪恶,但你必须回来,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认为小说家必须这样做。
人物周刊:小说家的职责是什么?是要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个误会,还是要拉近彼此的距离?
胡:这是一回事,更多的是同情,更多的是宽容。我觉得原谅是最难做到的,所以至少要理解。我觉得也许我的命运就是消除那些误解。在某种程度上,记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在沟通,在传播信息,然后加深人们的理解。
南方人物周刊太阳於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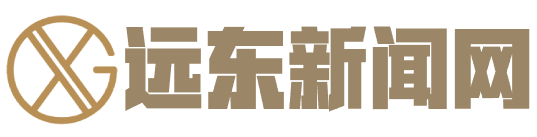
 新闻快讯
新闻快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