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 十九世纪 霍乱曾流布世界
导语:编者按: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
编者按: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他以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开始时,从许多方面来看,霍乱在全球蔓延的最重要表现是工业化带来的流行病模式的改变。这种疾病在孟加拉国已经流行了很长时间,并不时以流行病的方式从这里传播到印度和邻近地区。霍乱是一种由霍乱弧菌引起的严重传染病,霍乱弧菌是一种能在水中存活数周的病原体。如果霍乱弧菌被吞食而没有被酸性胃液杀死,它会在碱性肠道内迅速繁殖,往往在最初发病的几个小时内就产生剧烈反应——腹泻、呕吐、发烧甚至死亡。霍乱的致命速度令人震惊,当它流行时,没有人能摆脱对猝死的恐惧。此外,霍乱的症状特别可怕:严重的脱水使病人在几个小时内干燥得面目全非,微血管破裂使皮肤颜色变黑变蓝。当患者死亡时,情况尤其引人注目:他身体的恶化和加速就像一部慢镜头电影,提醒着旁观者死亡是多么的狰狞、恐怖和完全无法控制。从统计学上看,霍乱的影响时常很严重:1831年当霍乱第一次袭击开罗时,该城大约有13%的人因此命丧黄泉。这并非常态,欧洲城市中的疫病损失尽管从没有那么大,却不能降低这个杀手到来时带来的独特心理影响。霍乱似乎能够穿透任何隔离,绕过任何人为障碍:它随意而又主要在欧洲城市的下层选择自己的牺牲品。简而言之,在欧洲近代的经历中,霍乱既是异常可怕的又是独一无二的疫病。相应的社会反应也往往是极度恐慌而且影响深远。1817年,当霍乱疫情席卷加尔各答腹地时,这种疾病首先引起了欧洲的注意。之后,霍乱蔓延至印度其他地区,很快冲出了南亚次大陆与周边地区从未跨越的分界线,这也是其此前作为地方病活动的边界。也许,霍乱在印度半岛传播的旧方式正与英国殖民者强加的贸易和军事行动的新方式相交叉。因此,霍乱已经超越了它以前的边界,进入了陌生的地区,那里的人们缺乏基本的免疫力和应对霍乱的经验。从遥远的古代起,印度教的节庆就吸引着大量的朝圣者涌向恒河下游,而霍乱正是这里的地方疫病。于是,朝圣者有机会感染上霍乱及其他疾病;那些当时没有倒下的患者则可能把疫病带回各自的老家,在他们的故乡演变成一场场杀机四伏的霍乱流行,有时甚至对人口产生毁灭性冲击。霍乱与印度圣日的朝圣之旅至今如影随形。我们有把握认定,在1817 年之前的印度本土,虽然严格的习俗曾经相当成功地把霍乱传播限定在印度朝圣者中间,但它还是不时登船沿海路悄然出境,足迹远达中国。唯其如此,当霍乱在19 世纪初叶侵入中国时,中国人才没有把它视为新病*,尽管很长时间内人们没有在中国沿海地区见到它邪恶的身影。然而在1817 年,当一场暴烈的霍乱反复流行时,英国的船只和军队也在加尔各答出现,他们从那里进进出出,又把传染病带到了陌生的地方。霍乱沿着两条路线离开这个国家。一是土地,活动范围相对有限。在1816-1818年期间,在印度北部边境打了几场仗的英国军队将霍乱从他们在加尔各答的总部带走,交给了他们在尼泊尔和阿富汗的敌人。更猛烈的是霍乱的海上传播。1820-1822年间,船只将霍乱传播到锡兰、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中国和日本。位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马斯喀特就患上了这种疾病,它是由1821年一批旨在禁止奴隶贸易的英国探险队登陆造成的;霍乱随着奴隶贩子从马斯喀特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渗透。霍乱也进入波斯湾,渗透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继续向北进入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里海,在那里突然停止,可能是由于1823-1824年不寻常的冬天,而不是俄罗斯、土耳其或波斯的人为因素。霍乱在中国和日本停留了很长时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在1826年第二波疫情高潮之前,它是否真的从中国消失了。实际上,这一事件只是19 世纪30 年代霍乱大流行的前兆,那次大流行才使霍乱真正成为全球性的疫病。1826 年,一场新的霍乱出现于孟加拉,又迅速沿原来的线路折向南俄罗斯。随着俄罗斯对波斯的战争、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及1830—1831 年镇压波兰起义等一连串军事行动,又把霍乱于1831 年带到巴尔干,从这里再由船只传到英国。来年霍乱侵入爱尔兰,爱尔兰移民又把它带到加拿大,并南下美国和墨西哥。后来的疫情比第一次对欧洲腹地的袭击产生了更长期的影响。1831年,霍乱在穆斯林朝圣期间出现在麦加。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印度早已耳熟能详,不可避免地会重演,但这一次的地理范围要广得多,因为穆罕默德的追随者要么回到了西部的摩洛哥,要么回到了东部的棉兰老岛,或者介于两者之间。从那以后,直到1912年麦加和麦地那最后一次爆发霍乱,这种可怕的瘟疫一直伴随着穆斯林的朝圣活动,在1831年至1912年间发生了不下40次,也就是说平均每隔一年发生一次。当霍乱就这样将穆斯林的朝圣加入到以前印度教徒朝圣的传播路线时,印度之外的人们也就长期暴露在了霍乱的威胁面前。还有,18 世纪中期之后更先进的汽船和铁路运输所取得的成就之一,便是加快了霍乱从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传播的步伐。印度境外,尽管准确数字不得而知,但死于霍乱的人数在19 世纪肯定达到了数百万;印度境内,霍乱曾是并仍然是重要的疫病,造成的死亡比鼠疫多得多。只是印度对霍乱太过熟悉,并不会激起太大的社会恐慌。然而,印度以外的情况是另一回事。伊斯兰社会长期饱受瘟疫之苦,认为欧洲的隔离制度荒谬可笑。然而,对于埃及和其他受影响的伊斯兰国家来说,霍乱造成的死亡是如此出乎意料和可怕,社会冲击几乎与欧洲相同。他们的医学或宗教传统无法应对。霍乱引起的大范围恐慌有助于人们质疑伊斯兰世界的传统领导人和当局,并为他们接受欧洲医学铺平了道路。在欧洲肯定存在这样一些地方,那里曾被鼠疫光顾的经历,一直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并始终如此鲜活,以至于公众和机构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都较为适当,尽管方式有些原始。地中海欧洲的许多地方就是如此,在这些地方,宗教祈祷与医学检疫并行不悖,后者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立法的重要内容。在马赛,对1721年鼠疫的周年纪念,使人们对那场灾难的记忆一直栩栩如生,霍乱因此又成了再度强化基督教虔诚信念的理由。然而,在北欧,当出现疫情危机时,其传统行为准则尚未确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从圣彼得堡到巴黎,通常可以在各个地方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仪式化;要将这种社会紧张的表现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不容易。因此,人们不得不即兴发挥,或争论,或逃跑,或祈祷,威胁和祈祷。换句话说,有很多行为准则。面对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疫情威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有效的方式来应对。此后,19世纪霍乱恐慌的反复爆发,直接推动了保障城市卫生和公共卫生的立法实践。首先,霍乱为对立派别关于传染病理论的长期争论,增添了新的紧迫感。从希波克拉底以来,一些欧洲医生就坚持认为,疫病暴发是由来自死尸或其他腐烂物的瘴气所造成的。这些理论相信,当虚弱的人碰上瘴气时,罹患疾病就不可避免。在疟疾和以昆虫为媒介的其他疫病始终猖獗的地方,瘴气理论有着坚实的和令人满意的经验基础,起码看似如此。早在1546年,Fracastoro就提出了接触感染的病菌理论,与瘴气理论是对立的。但直到19世纪初,这一理论虽然为地中海制定检疫条例预防鼠疫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学术界始终处于弱势地位。1802年,瘟疫降临到派往圣多明各镇压杜桑·卢维杜尔起义的法国军队身上。短短几个月,黄热病等热带疾病彻底摧毁了这支33000人的精锐师,严重挫伤了拿破仑的狂妄野心,迫使他在1803年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这场瘟疫在侵蚀欧洲海外力量方面的戏剧性表现,为法国医学界的热带疾病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动力。1822年巴塞罗那爆发黄热病时,他们抓住机会进行重点实验,区分接触感染派和瘴气派的对错。尼古拉·切文领导的法国专家组对黄热病的流行模式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巴塞罗那的感染者没有接触病原体的可能性。因此,接触感染理论似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在接下来的50年间,医学改革派开始拆除地中海港口的永久隔离设施,认为它们只是迷信时代的遗存。由于那时缺少经验基础,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昆虫有可能是疾病的携带者,病菌理论似乎注定要成为历史的垃圾。尤其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把检疫制度看成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粗暴侵犯,并致力于清除这些所谓专制和罗马天主教愚昧的残余。然而在1854 年,一位叫约翰·斯诺的伦敦医生证明,暴发于伦敦某中央街区的霍乱,是如何可以追溯到某处被污染的饮用水源。遗憾的是,斯诺的证据大多是不连贯的细节;又值欧洲最严谨的知名医学专家刚刚明确否定了接触感染理论,斯诺的说法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多少注意。然而到19 世纪80 年代,随着显微镜对病原菌的发现,才戏剧性地扭转了这一边倒的学术舆论导向。第一批病原体是炭疽和肺结核,分别由巴斯德于1877-1879年和科赫于1882年发现。由于这两种传染病从未以明显的流行方式传播,发现它们并没有颠覆原本解释疫情的瘴气理论。然而,当科赫在1883年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导致霍乱的弧菌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果科赫是正确的,瘴气理论是错误的,至少在解释霍乱方面是错误的。既然博学的医生们已经接受瘴气理论对流行病的解释,科赫对霍乱病因的解释自然在专家当中遭到了坚决抵制。 迟至1892 年,甚至有一位着名的德国医生为证实病菌理论的谬误,喝下一大杯充满霍乱弧菌的水,并高兴地告诉他的同行对手,自己没有不良反应。他是幸运的,但他的行为无疑夸大了影响霍乱传播的不确定因素。在这位医生的例子中,可能是高度紧张导致他分泌了过多的胃酸,从而杀死了他吞下的霍乱弧菌。早在科赫的显微镜向医学界证明现代瘟疫之源以前,霍乱在美国和欧洲城市产生的震动,就为那些寻求改善城市卫生、住房、医疗设施和水源供应的改革者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做什么和如何做的范式就在身边。18 世纪欧洲政府还发现,士兵和水手的生命太过重要,不能无谓地消耗,特别是当简单而又不昂贵的措施就可以阻止瘟疫肆虐的时候。在众多的保健措施中,最著名、最有意义的就是喝柑橘汁预防坏血病。当航行在大洋彼岸的水手长期只吃缺乏维生素的食物时,就会被这种疾病缠住。早在1611年,柠檬和柑橘的治疗作用就被报纸推荐,然后被德高望重的名医引用,并在大量医学文献中被提及。当时因为柑橘汁通常很难获得,所以学术界推荐了其他的处理方法。直到18世纪末,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方法的特殊功效。事实上,甚至在英国海军医生詹姆斯·林达发表了他精心控制的实验结果,以证明新鲜柠檬和柑橘汁在治疗坏血病上的有效性之后,海军总部也没有做出反应。其原因部分是经济上的—柑橘汁昂贵而稀少,又无法储存太久;部分是因为海军机关相信别的治疗方法也许更有效,比如库克船长曾在太平洋上给船员吃的微酸的甘蓝菜。而且,当1795 年海军总部真的决定采用柑橘汁来预防坏血病,并为水手规定了每天的食量的时候,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生长于西印度的各种柑科莱姆果缺少必要的维生素,但却比地中海的柠檬价格便宜,于是英国海军饮用的是几乎毫无营养价值的莱姆果汁,并因此得到了“ 莱姆兵”的绰号。因此迟至1875 年,尽管有规定要喝定量的莱姆果汁,但坏血病的阴影仍笼罩着英国舰艇。尽管令人困惑和无效,但在18世纪下半叶,詹姆斯·琳达和其他英国海军医务人员在健康管理方面做出了其他重大改进:琳达敦促该船设立一个海水蒸馏器,以确保纯净饮用水的供应;此外,隔离新兵直到他们洗完澡穿上新制服,也是控制斑疹伤寒爆发的简单方法。此外,在琳达的指导下,还出台了使用奎宁治疗疟疾、禁止在夜间登上疟疾流行的海岸等规定。然而,陆军在卫生管理上的相应改进,比如关注水源供应、个人清洁、污秽处理系统等,却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因为陆军士兵从不会像船上的水手那样,完全隔离于外部传染源之外。但是,18 世纪的军队作为欧洲君主的最爱,既在统治者眼中很重要,又很容易自上而下地进行控制,他们的健康不可能不受益于越来越多的卫生条例,而卫生条例从保护士兵到面向普通大众只有一步之遥。这一转变,在欧洲大陆被有条不紊的德皇的臣仆们做到了,如果实践尚不够彻底的话,至少在原则上实现了。最有影响的是约翰·彼得·弗兰克,他于1779—1819 年间出版的关于医疗制度的六卷本着作,在统治阶层中引起了广泛而良好的反应,特别是在那些已经认识到国力的根本在于臣民数量和体力的统治者和政府官员中间。欧洲政治史与职业常备军的关系更值得历史学家关注。显然,欧洲大陆君主专制的兴起,有赖于跟随君主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无论是冬季还是夏季,无论是战场还是军营,军队的健康都有赖于卫生保健体系的发展,将流行性疾病的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制服形象和仪式清洁规则无疑是保证欧洲军队健康的方式。显然,18世纪是这种做法变成规定的时期,其影响历史性地改变了以经验治军的现状。似乎没有人讨论过约翰·彼得·弗兰克博士深厚的医学理论与现任军官制定的军事法规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些规定占用多少时间,它们都保证了他们的健康,并使他们在作战能力方面得到严格的训练。就像在军事管理领域的诸多表现一样,法国人也一直是卫生规范的确立者。18 世纪早期,法国皇家政府就建立了军队医院和医护学校。18世纪70 年代,一个现代的特殊医护部队建立了,其关键的创新是医生可以全职服务于新建的军队医疗机构,像一般军官那样晋升军衔。而不再像从前,只是在出现危急情况或迫在眉睫的战争时,才临时应召入伍。法国军队的医疗机构专业化带来的好处,充分展现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中。从巴黎贫民窟和偏远的乡村征召来的年轻人,一起源源不断地充实着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乃至各个阶层。然而,尽管新兵的疾病经历和随身携带的抗体各种各样,但医疗团队有能力阻止大规模的疫病暴发,并利用新的发明,比如公布于1789 年的琴纳的疫苗接种术,来提高其负责照顾的士兵的健康水平。否则,作为拿破仑时代特征的大规模陆战就不可能发生。同样,英国海军能够长年累月地封锁法国港口,其对柠檬汁的依赖几乎等同于枪炮。从军事医学的成就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卫生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组织问题。无论如何,英国的自由主义偏见根深蒂固,人们认为这些制度侵犯了个人随意处置财产的权利。只要疫情传播理论仍有争议,双方就很难在实质性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人们对霍乱的恐惧。面对死亡的威胁,不作为很难解释,公共卫生机构只能尽快结束陈腐的争论和顽固的冲突。霍乱于1832 年在英国的首次暴发,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但由于委员会委员从地方选出又没有薪给,因此通常缺少专业知识和合法权力来改变当地的生活环境;况且,不是每个委员都认为肮脏和疫病有什么关联。比较起来,1848 年霍乱的再次暴发引起的社会反应更为重要。那一年,就在霍乱再度降临英国的前一周,国会授权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当时,亚洲霍乱的可怕景象已经牵动了公众注意力长达一年。毫无疑问,正是对霍乱复发的担心加快了国会的行动。中央卫生委员会颁布了一些对公共卫生有深远影响的计划。这些计划已经被一个改革派团体大力提倡了10多年。这个团体非常活跃,其成员中有许多著名的医疗改革倡导者。利用国会授予的法律权力,中央卫生委员会已经消除了英国城市的众多污染源,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供水和下水道系统。下水道不是新鲜事物,其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但直到19世纪40年代,下水道还只是一端连着大量的排泄口的加长了的化粪池。因为供水严格受限,除了在多雨期,其他时候水在里面的流动是缓慢的,所以这种下水道沉积的秽物必须定期清理。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想法,主要由一位名叫爱德温·查德威克的热诚的功利主义改革者所提倡。他的想法是,用光滑的陶管建成狭窄的排水管,注入足够的水把废物冲向远离人类居住地的储存池,在这里,按查德威克的设想,污物可以进行加工,卖给农民做肥料。如果这一计划要成功实施,就需要铺设新的排水管和下水道系统,开发更强大的泵,并强行拆除旧的下水道系统,以便有足够的压力向住宅供水。为了保持有效的排放,水管和下水管必须铺设直,这意味着入侵一些私人领地。对当时很多英国人来说,这些似乎是对他们权利的不合理侵犯,项目所需的资金将是巨大的。因此,人们只有因为对霍乱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才能克服根深蒂固的反对障碍。最初,查德威克的想法连一半都未能兑现,因为在把污物卖给农民做肥料一事上,他就无法做出经济上的合理安排。现实是,农民可以买到人造肥料以及来自智利的海鸟粪,这种肥料比查德威克的下水道污物使用起来更便利。可行的替代方法是把污物排到方便的水域,其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后来,又花了半个世纪才研制出处理污物的有效方法,以使其不再散发那么刺鼻的恶臭;而大规模地设立这样的处理系统,即便是在繁荣而管理有序的城市中也要等到20 世纪。虽说查德威克未能实现他的全部计划,但他指导下的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其存在的1848—1854 年间的确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将工业革命所造就的新城市治理得更加符合健康原则。而且,对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的城市社会来说,新的排水系统并非昂贵得难以承受。但在长期使用人粪作肥料的亚洲,新的污物处理系统始终没有普及。这一体系向其他西方国家的输出相对较快,尽管经常需要利用霍乱感染的紧迫危险,迫使当地既得利益者对医疗改革举措做出妥协。在美国,面对新的霍乱威胁,1866年在纽约成立了一个以英国为基地的卫生委员会。在没有这种电力的情况下,像汉堡这样的大城市坚持将昂贵的供水系统的重建计划推迟到1892年。当时,霍乱的光顾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它是传播疾病的污染水源。原因如下:汉堡作为一个古老的自由城市,即使在新德意志帝国时期也仍然是自治的,未经处理直接从易北河取水。它对面是阿尔托纳城,属于普鲁士。当地政府为居民建立了一个滤水厂。1892年,当霍乱在汉堡爆发时,它只沿着两个城市的分界线汉堡一侧的街道传播,而另一侧阿尔托纳的人们却毫发无损。应该说空瘴气理论强调的气土条件在城市边界两侧是一样的。然而,霍乱传播的趋势比有意设计的趋势更雄辩,显示了供水在界定疫情范围中的重要性,怀疑论者最终哑口无言。此后,为了消除细菌感染,汉堡等地开始系统地净化城市供水,而霍乱真的再也没有回到欧洲。显然,从决定引进给排水系统到完成必要的设施之间,总会有相当的时间差。而19 世纪末的西方所有大城市,无不在努力接近大不列颠在1848—1854 年首倡的新的卫生和水源管理标准,城市生活要比以往更加远离疾病。不仅是霍乱和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其他一般水媒传染病也在急剧减少。由此,导致儿童死亡的疫病威胁,在人口统计上也日益趋于无足轻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城市很少允许所有人享有健康的饮用水供应和下水道系统;然而,即使在那里,随着水污染的危害被更广泛地理解,简单的预防措施,如烹饪饮用水和定期检测水体中的细菌污染,在防止与水传播传染病的全面接触方面相当有效。虽然公共卫生管理机构不能坚持有效的细菌观察,但在很多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就更难了。然而,用于避免大规模致命疾病的方法和知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当地方性霍乱或其他致命疾病发生时,富裕国家通常会发起一些国际行动,并邀请医疗专家帮助地方当局控制疾病。从那以后,即使在从未铺设污水系统的城市,公共卫生的一些好处也迅速得到了证明。本文摘自《瘟疫与人》,作者: 威廉·麦克尼尔,译者: 余新忠 / 毕会成,中信出版·见识城邦2018年5月版
免责申明:以上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不代表远东新闻网立场!登载此文只为提供信息参考,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目的。如有侵权或内容不符,请联系我们处理,谢谢合作!
当前文章地址:https://www.ydj6688.com/news/438753.html 感谢你把文章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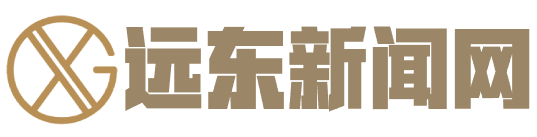
 新闻快讯
新闻快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