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围城 一百个人的民国三十七年围城往事
这篇文章是竞赛的前50名决赛选手之一
文 | 陈锐2014年夏天,我决定开始一段漫长的旅程,寻找一群历史上鲜为人知的见证人,这发生在66年前。5年过去了,这百余名垂暮者正在陆续离世,寻找并倾听他们的过程,永远记录下来。我费尽心思从这些人中挑选出下面的“故事”,浓缩成一万字的文字,试图给历史上的普通人多一次机会——掀开面纱,让发生的事情一一浮现。1. 民国三十七年的一张全家合影:逃难①我用手挡住了眼前落日耀眼的光芒,遮阳板也不再工作了。汽车一路飞驰,几年后想起那一瞬间,后脑勺还在痛。
就为了赶一个好时机——“舅舅又不想说了,我做了半天工作,你来之前……”,司机说。我感激的看着他,如果没有他,我翻遍再多的史料,也无缘得见一张珍贵无比的老照片——66年前事件发生时,一张难民在街边找人拍的全家合影。这个网名“好好儿活着”,名片上写着来自北京“中国英国商会”的年轻人,在我们见面前,手机上发来一句话:“你帮我实现了一个愿望,给了他们一个交代……”这是一张应该收录在国家档案馆甚至世界历史博物馆的照片:一个留着胡子的老人,两个中年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孩子,一共七个人,三代人,背景是砖墙,搭了一条窄窄的深色背景布。这个季节是中国东北的凉爽季节,中秋节...一个即将“旅行”的家庭的形象是固定的,66年前——现在是77年。“照片是逃难以前照的,因为听说出卡子要照片。”王红志板着脸说,上帝保佑好时光。2014年11月1日下午,当我到达目的地秦皇岛时,老人终于开口了。但是他那淡定的态度告诉我,他跟侄子说了那么多次都是普通的家事,那他为什么还要吸引记者来听呢?“长春-秦皇岛”,多么熟悉的路线,当一家人走出喀孜回到老家时,他坐在沙发上,靠着身子,仿佛是一个陌生人。“长春最东边,东大桥还有吗?”他说我们不过是想借道长春回老家,住东大桥桃源路的一个表叔也和我们一起走,就是照片上左边那个男人。你们是哪里人?农安福龙泉。1945年,日本投降,学习失败,所有的商人都关门了。穿越东北的爷爷决定回河北老家。一点一点回家——我妈生病了,肺心病;我父亲胆小,被枪击吓到,枪响时抽搐;两个妹妹还年轻。哪一年出来的?那是1947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农安到长春,当时火车无法通行。我们乘车去了长春。没想到长春的火车无法通行。当时,新闻被封锁了...刚到长春时还挺好,没打呢,后来困住了,吃的越来越困难,通货膨胀,啥都不值钱,钱也不值钱了。2. 重返竭家窑战场,拼命厮杀民国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与日本作战时,东北的历史被切断,被称为满洲国,山海关成为国境线。光复后,“满洲国”从历史规模上消失了,日本人离开了,等待已久的国民政府来了,但共产党也来了,战争恢复了。东北成为整个中国战争局势的重中之重。王洪志一家从农安向长春赶路时,“火车不通了”,当时发生的,或许是整个东北的一个缩影。1946年底,当农安在龙泉和段家窑遭遇时,国共两党在东北争夺一场著名的战役。与历史交流的最好方式,就是走近每一个历史场景,倾听经历过的人,还原事件发生时的场景——伟大历史的“冰山一角”。“打竭家窑那年,我十四岁。1946年阴历十月十六,阳历11月9日,外头有大月亮,炮响,我脑瓜子就往炕洞子里钻,怕把房子崩倒了,就在我们家这打的,旁边就是竭家大院。”魏汉成戴着一幅深度的近视眼睛,瘦的不成样子,可是记忆的力量啊,如同昨天发生:“就家门口这山坡子,打完我们去捡子弹、手榴弹……背个大粪筐,一划拉一下子。沟底,都是子弹壳,国民党飞机往下打机关炮。”老魏从炕沿上站起身,手指窗外,五十米开外的小道,仿佛子弹仍在呼啸,“伤员都抬这屋来了,脑袋淌血。我们有个北炕,摆一炕,脑袋朝北,脚朝南,脚都包着。脚丫子丢了的,活着不会说话的……没有担架,把各家门板都摘下来了。竭家窑这,打了一天半,好像死了九百人,他们自己清点的。后来死的都拉走,埋肉丘坟,我们一家出一个人,俩人抬一个,用马车拉走。那时候有九个肉丘坟,一个坟埋一百来人。”竭家窑大院没死的中央军,国民党用飞机接走了。飞机来,老百姓顺着大沟跑,飞机没打老百姓。“他们的武器装备真好,村里现在还有当年留下来的钢盔和弹壳……”时光镌刻、眷恋、遗留在老物件上,生了锈的武器符号,在和平年代的阳光下成了满腹心事的“历史道具”:钢盔上有一个弹孔的痕迹,那个头部中弹的士兵或毙命当场或如果有着千万分之一的幸运存活下来的话,今昔又在何处?炮弹壳包裹了厚厚一层垃圾物质,落草乡野便大多与文物的待遇终身无缘;废弃的子弹壳在我眼中还在散发着火药的轻烟;另有一联保存完好未上膛的旧弹夹,忽然闪现在眼前,不禁打了个寒战。参加战斗的中国共产党老兵云玉德,也是1946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解放长春的见证者。“我的一只眼睛,就是在竭家窑遭遇战受的伤……我是1945年‘光复’后在农安当的兵——解放军,第一仗就是1946年解放长春;打完长春奔四平,参加了第三次打四平;打完四平,一直退到黑龙江……国民党上边有飞机,下边有坦克、汽车,我们一边撤退一边扒铁道,然后上火车,往北走。到了1947年,解放军从外围向长春推进,我们接到命令打农安,结果在伏龙泉竭家窑,遭遇战。遇着了,就开始打,枪林弹雨,密集的很,一颗子弹擦着我的脸就过去了,在眼睛部位,瞬间就烤化了一个眼球”……伤疤藏在身体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宿主生长或消退,不被外人察觉。感谢时间的馈赠,让我知道此刻坐在我对面的老兵看着我时,我眼中挥之不去的阴影。3. 四平难民,逃出战场又进围城“我九岁的时候没有父亲。我父亲被抓去当劳工,死在抚顺煤矿的万人坑里。十二岁没妈,是攻打四平城,我家在四平,为了躲战争,从四平逃往长春。住了之后,有一点点破烂,得清理一下卖掉。妈妈把我们姐弟俩送到二道河子区民丰五中长春姐姐家,然后就回去了。结果四平和徐进不准离开……1946年,我十二岁。我妈攻打四平市的时候死了。在战争年代,我不能说我死在哪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潘玉兰把胳膊拄在麻将桌上,若有所思的看着我,我一时间也恍惚了片刻。约半个小时前,我一路打听着找到她的家,面对着不速之客、一个年轻人的到访,潘玉兰很快定住了神,因为我的问题,让她回到了生命记忆中久违的“沉睡区”。“后来,我听说我的八面城极其悲惨。不知道四平之战是怎么打的。就说你想开枪打。那一年,有一趟从四平到长春的火车。躲在四平,没想到被困长春...我哥哥在长春去世了。我侄子也在长春饿死了。他已经饿死了。如果他不爬夹子,我们三个就都没了。”1948年,围的最严重那会儿,晚上10点以后,听广播喇叭,是那边封锁线传过来的:同志们,逃活命吧,哪天哪日放卡子,哪个哪个卡子放。是指着市里往外走,有卡子,“我们在城东,卡子外,二道河子区,顺着街边子,穿大地,抄近道,也不知道哪是哪,听到枪响就往地垄沟爬。我们是三口人一起出来的,我和姐姐、姐夫——旧历八月十七,那天是我生日。”离开之前,是什么感觉?民丰五,太可惜了。昨晚,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去讨饭,谁能给?我还没吃饭...第二天我开门的时候,我妈仨就死在那里了。我不能走路,我饿了。孩子瘦弱的大脑脖子小,太脆弱了。他死的时候被拖进沟里,没人收尸。二道河子就像一个“四不在乎”的区域。离开城市前,国民党白天来了,拿着枪走在街上。晚上他换了共产党,猫穿了个小蛮腰,放在阴沟里,嗖嗖地跑。“年轻无知的时候,我们有时会说:“看,共产党来了。大人说:不要出声。害怕枪。"4.7月,不辞而别的父亲
。当然也担心长春围困的太久了,我们……过不下去了。那是十月中旬,我们四个人从剪辑中出来,天气很冷。我只记得去喀孜的路上人很多,要在国民党卫队门口搜身。我妈离家的时候,赶紧在身上戴了块表,他们就拿走了。离开的时候推了一辆车,我和妹妹坐在车里,妈妈抱着妹妹…我们在卡哨大约住了四天,有一天赶上大雨,妈妈穿着棉袄,抱着妹妹,在雨地中。我和姐姐躺在车里,姐姐发烧,别人用野菜做了一碗菜汤,来给姐姐喝,没有我的份儿。我当时对那一碗野菜汤,印象特别深刻,想喝,但是没有我的份儿,很少。妈妈说,姐姐发烧了,只能给她喝。”“我的父亲王光体,1946年至1948年在长春当记者,举办过周座谈会。1948年底东北国民党政权垮台前,他离开了妻子和女儿。后来,我从父亲的作品中得知,他从剪辑中出来后,一路走到了天津、青岛、厦门和台湾省……”生命像一粒种子,战争年代扬起的沙尘,可以将一个人吹向无限遥远的他乡,终生回不了头。70年后,一个八旬老人,吉林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周励,全世界寻找父亲生前的活动轨迹,整理父亲的创作历程,试图从中体谅到父亲在那一年的不告而别,以此告慰含辛茹苦、阴阳两隔的母亲,以及漂泊终生都没能回到故土的父亲。以下记录来自1937年9月天津《伊势日报》。半个多世纪后,这份报纸的副本被归还给了记录者的家人。我有幸用自己的双手触摸它的温度,我把每一个字空都告诉了我的心:
“1948年8月3日,经过两次失败的尝试,终于在第三次成功爬出了卡子……长春,这座在自己生命史上曾有过深刻记忆的城,因为饥饿,不得不离开。笔杆当不了枪杆,文章解决不了饥饿,事实不得不走,但是扔下了那些与阵地共存亡的战友,抛开那座花园一般美丽的城,始终是心戚戚,难得释然!”与周励父亲同行的还有长春大学的学生,他们几经周折,从长春城东的方向始终突破不了封锁线,甚至两次都被围城部队押送回二道河子放下。第三次,改向正南方出发——这在一开始曾被放弃和试图绕开的、聚集难民太多、不容易走的“洪熙街”卡哨……积累了前两次保送的经验,这一次,他们找到了一个熟悉封锁区地理的人——“职业亡命之徒”,他们“敏感,可以说是天才禀赋。快走、过草地、钻进庄稼、涉水、爬山,都保持同样的速度。因为他太专注于听和看前面的路,他很容易不回头,照顾我们...他对哨子配置状态的熟悉程度令人钦佩。有好几次,哨子在独立式房屋的左边角落,我们从右边角落悄悄走过来。”领导答应带他们去长春东南50英里的新立城。离开封锁线50英里后,他给领导送去了一些农用衣物作为路费。”虽然他不满意,但还是勉强接受了。那时,除了一点食物,我们身无分文。”5.东北流亡学生两个青年的路
,到处都管饭。但实在想走也给放行,我就拿着路条继续赶路……”那次“长征”,沿着铁路,跨过大凌河,绕过洋河——洋河上没有别的桥,就是一座铁路桥,一个支架,只有铁轨和枕木。“我用双手扶着栏杆,下面,几十米远。我不敢看洋河。有两三百米长的大铁路桥挂在空去锦州上火车。基本上开始向山海关开放了。去北京。你走了多少天了……”“北京,有国民政府专门接收东北流亡学生的机构。打天津我赶上了,炮火轰轰轰,我在东局子,天津东边,打的不算激烈,那阵国民党就已经不行了,‘四野’的大兵压境了”。卞家院的旧挂钟在围城期间走得那么慢,时间被记录和遗忘,但人们仍然记得一切。国家记忆对国家伟大历史的修复是一剂解药,在那里,弱点被修复,个人的伤疤被还给时代,这样才能期待更远更长的路。边家大院的年轻人,在围城初期上路去寻找正统,而更多的年轻人还在城内,混乱无序的战时状态,生长出了一种异样的自由,“我1948年7月高中毕业后,长春就比较困难了,开始有饿死的人,我们的米也越来越紧张,在家没啥事,一个表哥在国民党新七军当文官,让我去他那里,混口饭吃,办公室就他一人,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拿着碗去,这样能够给家里省下点粮食。”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孙景春,面前摆着一张泛黄却保存完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心里埋藏的往事沉睡了66年,终于一字一句的缓缓道来。“在表哥家混,有十天,然后国民党长春大学招生。在城外,但是在城里,这些东西都不会影响,所以就做吧。虽然我招生了,但是我被录取了,但是我不能去上课。当时我们学校系今天在东北师范大学医院对面,在友谊商店,学校已经搬走,搬到天津去了。当时沈阳仍被国民党占领。我们必须先向沈阳报告,然后再转移到天津……”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六日”,坐在我对面的老人说,这是后补的通知书,事实上他们在8月下旬就从长春出了卡子,去沈阳报道。可是,出发时告知的目的地,半道改了——被另一方接收,去了吉林解放区。6.围城里的人,命运的几何
东北是一片向寒而生的土地,千百年来,历代蛮荒,归统满清,民国不保,疆土外割,终至“光复”,这里又成了两股势力角逐的战场,孰王孰寇,百姓怎知晓?命过几晌,只能看天。太阳在扶壁外落下。你知道农村堆着什么庄稼吗?刚割下的庄稼一捆捆地堆在一起,头叉在一起,站在地上,形成一个垛,外面有缝,里面有空。如果我们能把人藏起来,我们就藏在那里。有两张婴儿床,都是我家的。一个婴儿床有五个,另一个大约有四个。我不记得了。那年我只有五岁。太阳下坎那会,我记得真清楚,我从里边向外看。看见一个小男孩,从那边走过来,大脑袋,小细脖。我们一家人都看见了。我妈悄悄念叨,别过来,别过来……。我往外看,太阳光很晃眼,一个国民党兵喊:小孩,站住,会唱歌吗?上去,唱一个,我给你窝头吃。小男孩,努力往墙上爬,可是他太小了,又没有力气,爬半截掉下来,再爬上去又掉下来,终于踉踉跄跄站上了墙头。国民党兵: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毛”字刚出口,“啪”的一枪,男孩应声倒下。我好难过,二哥说我出去整死他,我妈死死按住二哥,我们仰头看夕阳下土墙拖着长长的影子。第二天,又是一个日落,全家又饿了一天。一片寂静,除了外面的国民党士兵,他们来了又走了一会儿。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们正处于困境之中。事实上,每个扶壁上可能都有人。这些人不能回家,村子已经被军队征用了。经常出去找吃的二哥说有四条封锁线,没人想逃...我很难记起那段时间有多长或多短。突然,从扶壁外面空进来一个小铁盆。它太大了,看起来很好。这个盆是我们家多年留下的。盆里有什么?大豆,一些叶子,一些盐,还有一起。只听外面一个国民党士兵说:别说话。你能不感动吗?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一幕,救人。下一班换班时,我听到战士问其他人:“还有剩下的吗?”“你不是吃饱了吗?”“洒了,掉在地上点下……”张桂凤②剪辑里的十四天十四夜。14天,我被困在红西街的剪辑里。在这个“三不管”的地方,我进去逃出来的时候还有点力气。后来...我家在一个大房框子里,这一堆一家,那一堆一家。我弟弟死的那天,不知道为啥,大房框子里,死好几十人。我母亲第一个发现我弟弟死了,我母亲的哭,好像还有点力气,把他们震醒了,大家反手一摸,越看死的越多……没力气往出拖,新死的人,就在我们旁边,到最后,你可能都没看见过大尾巴蛆,顺着那鼻子眼往出爬,晚上,冰冰凉啊,我一拱……吃粪豆。有一天,我在井边,正要去打水喝。低头一看,发现一堆屎,里面混着很多没消化好的炒黄豆瓣菜。我蹲在一旁看着。过了一会儿,稀薄的水变干了。我把黄色的豆瓣一个个挑出来,有三四十片花瓣。然后我去井边,用清水洗了洗。闻了之后,没什么奇怪的味道。我把少量放在嘴里。嚼了很久,我咽了下去。头顶的飞机。人们说飞机来了,就有希望了。飞机来,照相,看死的多,就放人,看死的少,就不放。“飞机来了,飞机来了,”他们喊。双膀的飞机,好像门、窗户、人,都能看见。人们互相搀扶,都是跪姿的,“八路军,救命……”,说是在喊,但是声音出不来。飞机很低空,在那里盘旋了几分钟,然后离开了。当时,我没有认出天空和白旗。如果是国民党的飞机,即使有天空和白旗,我大概也没把它当旗看。彩旗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每次打开剪辑之前,飞机都要走,拍照,听里面的人说话。沙秀杰我想你,妈妈!我和妈妈没有家庭,没有生意,没有亲戚。1948年,我被围困在长春城,母亲在东大桥外,国共两党被空个孩子夹在中间。后来,我饿死了,被扔进了万人坑。等银行那打完仗③,大伙都热火朝天,庆祝解放,我出去找我妈。有个认识的人说:看看你妈去吧,你妈没了,在东大桥万人坑。走到东桥,大坑...人死了,老了。看看周围,什么都做,臭哄哄的。大家捂着嘴去看。有个不体面的老太太,说你妈饿死了。“她死的时候,跪在河边喊,小玲子小玲子,我再也看不见你了,天天哭,天天喊,然后眼睛就瞎了。”遍地都是尸首,根本认不出来谁是谁。我妈的特点,有白头发,才三十多岁。也不知道哪个是我妈,不敢看,十七岁,不立事。找了一个有头发的,拽起来就说是了。然后搁席子卷着,用马车拉回来,直接送到宋家洼子,找到一块庄稼地,山坡底下,用土埋上,拍吧拍吧,坟头没写名,也没立碑,后来就找不着了。毕竟也不是我妈,我以后也没去填过土。杨我父亲先饿死,接着是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一共饿死四口。剩下母亲和我。母亲小脚,哪能走?我就爬出去,什么葫芦秧啊,能吃的我都吃,药不死就往嘴里塞,再给我妈带回来。现在不是夏天,天热的时候,所有的死人都生气了。有一天下雨,半夜12点我在外面。用现在的话说,我去偷别人的东西。是我,一个14岁的孩子,半夜回家,突然摔倒,倒在死人肚子里...尸体发作了,蛆在我的胳膊上,在水里洗...我就是一直没出卡子。要是没有我母亲,我几个卡子都爬出去了,能出去。我们家,死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坟。张继昌1948年7月的长春,尸体多,下雨,泡着,泡完就发,肚子都这么高,圆溜溜的,青紫色,凑近细看有红血管,真亮的。等到太阳出来一晒,嘭!爆了,那味儿啊,实在是,太难闻了……围城里的空气,就是这种,热乎嘟的腐臭味,成天都有,臭的不得了。盼下雨,下一场雨,好一点。张军7. 兵临城下的家书,投诚和起义去往广州的路程,是我在大陆寻访亲历者最远的一段。2003和2008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分别以“围城家书”为题材,出版了两本书——《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和《兵临城下的家书》,信和照片的主人,正是当年国民党守城部队的官兵。历史的舞台,从来没有谁曾缺席,多的是被遗忘或大潮掩盖。广州,远征军老兵,也是东北解放战争的见证者,梁振仁。他写给女友“毕”的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表,这让他困惑了很久。“如果问我自己的意见,我不同意发。”。吉林省档案馆只给了他一张收藏证书和一套仿真件,原件信件和照片属于国家档案馆。“当时只知道要去东北接收,可能会和共产党有摩擦。可是到了东北,才知道要打仗了,心里难受。我们对共产党没有仇恨。东北打仗和缅甸打日本是两码事。他们都是自己人,情绪和斗志各不相同。
1948年5月大房身机场失守、长春被围之前,我们去小合隆抢粮,长春西北方向。我们沿着铁路线打,这是我们刚进东北的时候,吃的第一个亏。他们的战士很奇怪,没有重武器,就冲锋,冲锋还抑上,往高爬,我们就很奇怪,这些人这么不怕死啊?完全不符合步兵操练要求。我们的轻重武器都有,一个排里面就有两门炮。五月到十月,我们的日子?一般来说,交流没有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收到消息。我们知道山海关在那里玩,锦州在这里玩。后来锦州沦陷,我们就完蛋了。东北人关上了‘门’。那年我23岁。我是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谍报队长。谍报队,跟着团指挥部一起,没有战斗任务,只是侦察。就是尽量派人出去,穿便衣,到卡哨以外的地区,‘三不管’地带,有老百姓从敌占区逃过来,我们收集这些人沿途的经历,什么地方有八路军等情报……这些难民要进城的不多,多是要上别的地方去。防守长春时要紧张,随时准备用剑用枪。如果敌人来了,他们就会遭殃。这是一首让我们攻击的歌。回望现在被围困的长春城,那些普通人。"梁老先生说,长春,一出来,就再没有回去过。1948年放下武器,他们算投诚,新七军,当时就去了吉林,他是尉官……斯大林死的那年1953年,把他送回了广州。“我手上有投诚证明书,还有因长春的这段经历被判过反革命罪之后的无罪判决书”。江西九江人,另一封家书的主人李建平,是国民党守军第六十军的一名军官,也是一名起义者。信中,人的长相依旧停留在同一年,脱帽胸前,民国青年更配军装,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脉络。李东阳建平怀念家乡,怀念父亲的遗体。他形容自己漂泊在遥远的东北边陲,长春是一片孤独的海洋,“连飞都飞不起来”,“在激烈的外围战争中铁鸟也飞不下来”...书中的信很短,只有一页多一点。“本来历史对于我,除了人,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文化大革命,抄家,墙皮都撬开了,虽然你起义了,但是你过去是国民党啊……《家书》中的这张照片,是长春给我留下来的。”李健平声音洪亮,往事在他那里,像吱吱嘎嘎吞吐的放映机。“去长春之前,我们第60军驻扎在吉林。其实长春的苦很简单,就是没饭吃,剩下的都一样。甚至唱歌跳舞。中央银行四楼的大舞厅每天都有舞会,直到1948年7月和8月。这些国民党军官什么也没吃,和我们一样,吃饱了。当然,没有肉吃,也没有奶喝。士兵?讲良心,他们也有饭吃。广州的梁先生,他们新七军的情况比我们好...
唯一不同就是,老百姓没有吃的。有一次,我在斯大林广场中央银行附近,什么街我记不住了,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两手扶着墙,从这边走到那边,我知道,是饿的,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赶紧盛了一碗粥,东北那种大海碗,端给她。女孩子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去,我一看,炕上躺着一大家子人,爷爷奶奶爹妈还有一个弟弟,摆的整整齐齐。一家六口,就剩她一个。她低头把粥吃下去,吃完了以后,万万多谢,说‘我还能,挺个一两天’。如果有力量,我会长期给她吃的,可是第二天我就不去了……” 8.台北,一个失忆的老太太去台湾,是追着历史指引的路径,我要去找一找“战败”的一方,看一看他们背井离乡的海岛。包里有一本书,书里有一张照片,是围城期间“活捉李弘”字样的钱币照片。然而我却一无所知,随着搜寻的深入,我知道最终被担架抬出长春围城的新七军军长李洪,原来是一位“远征将军”。在东北内战的漩涡之前,他们正在远征印缅战场。经历了长春围城之后,李鸿将军辗转至台湾追随孙立人,却被当作共产党的“匪谍”一关就是25年,出狱后十年有余,于1988年病逝于台南。“长春围城,我爸爸亲口跟我讲,他跟老蒋说,校长,东北可能不容易守住了,我们退到关内去……结果老蒋说,你们守,到时候我支援你们,用空军,空投。然后没办法兑现了,就希望,守不住你们就自杀。”李鸿将军的儿子李定安先生说,“败走台湾的人心里都明白,丢掉大陆的责任,哪里是几个将军扛得起来的?”“我父亲说,围城之初,四个老母亲的空救不了被围困的守军。后来蒋介石干脆放弃了诺言,军民饥寒交迫,十几万人病死饿死。他父亲的一些下属甚至认为姜根本就想消灭军队,事实并非如此,但至少是想削弱军队。第60军曾泽生部首先投降后,共产党人转而对付新七军。后来,共产党军队的冲锋队有一次侵入新七军总部,大喊:‘活捉李红!’当时我父亲还拿了一把卡宾枪杀了好几个人,还调转加强警卫清除。奶奶曾经说过:当时已经是严冬,长春被死神围困,粮食和能源短缺非常严重。我父亲出去巡逻时,他不忍看到这一幕。但是我无能为力。他跟着士兵吃米糠,抵抗力弱。他患了伤寒。这期间,司令员郑洞国将军到新七军视察,看他病了,以为他是故意装病。最后,部队由副司令员决定,向共产党投降。奶奶说长春解放后,共产党人用良药治好了他们的父亲。如果没有,他可能会在临终前死去。"“我父亲来到长春,见到了我母亲。我的母亲马毕业于长白师范学院音乐系。她是满族人,正宗黄旗,还是个格格。她在父亲担任长春卫戍司令时认识了他。后来,兵团司令员郑洞国作为见证人举行了婚礼。1948年我父亲被俘时,我母亲怀孕了。后来在哈尔滨的战俘营,我妈生了我妹妹。1950年,我在台北阳明山看守所出生时,被点名为犯人。
我的母亲,因为她过去经历了一系列的恐吓和刺激,即使过了五六十年,她仍然会陷入失去理智前的兴奋和恐慌。"
去看这个失忆的老人,屋子里的日常,老人的味道,一个外籍女佣,倘再早几年前,还会有一只小狗的陪伴。老夫人安静的坐在黑色沙发里,目光是那种无物的深邃……当记忆沉入海底,人生都成了泡影?我一时间觉得这很难接受。我多想眼前的老人能开口说话。“妈妈!东北的小姐,来看你了!她姓陈,陈小姐。她来自长春。长春。长春。吉林,吉林”。老太太只是微笑。她笑起来很美。“身体很好,除了脑袋忘了。她每天游泳,直到八十多岁。父亲去世后,母亲申请退休,独自加入了一个旅行团,去世界各地游玩。大陆也去了很多地方。”说话间,老夫人笑的像个小孩,这真打动我,像一个人回到了最初……记忆深处,可还记得东北,长春?“我与母亲生活了一个甲子,如今,遗忘,抹去了一切苦难!”“我们过去称之为阿尔茨海默病,这种病不受尊重,后来改名为痴呆。大脑的记忆,就像被橡皮擦擦掉一样,已经被一个个抹去了。当你得了这种病,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忘记,老人会开始怀疑,认为你在偷东西。我明明放在这里,你从我身边拿走了,或者你摸了我的钱包什么的,然后就慢慢开始了。然后在中间,有一个躁动期,有时会有攻击性、辱骂性和不稳定性。门上的锁当时是钉在她身上的,因为她半夜跑出去,被警察送了好几次回来。我们不知道我睡在这里睡着了。结果电话来了,我才意识到她已经跑出去了。”定安先生帮我和老夫人拍照合影,很奇妙,老人转过头,一直看我,一直看我。她坐在沙发里,我靠在沙发沿上,比较高,她抬头一直看我,然后笑。9.夹,地球没有出口去日本,同样是追着历史指引的路径,和中国东北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日本,那里生活着一个人群,是在1945年“光复”之后没能及时回国,因此经历了东北解放战争的日本移民。我要去找的,是在1948年,滞留在长春围城的一位日籍老人小代,当年只是个七岁的孩子。我甚至没有语言不通的担心,因为长春是这个孩子的出生地,中文占据了其幼儿教育时类母语的天时与地利,在见面之前,我们的邮件都是用中文写就的。东京之行,对我来说,是这漫长旅程的终点。目击者的强烈记忆和中国人的纪实语言,让试图保留这段历史的人松了一口气。“1947年10月,长春街头突然断电。煤气也停了。自来水也停了。
1948年的新年一过,可以听到远方的枪炮声。枪炮声几乎没有改变它的位置,只是缩短了与下一次枪炮声的间隔,但总是在远处响着。过春节的时候,逐渐延长了间隔,最后干脆停止了。八路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把包围圈推进长春。很快,八路军突然停止了活动,长春再次被遗弃在寒冷、寂静的黑暗中。窗户上挂着冰花。饿死的人开始出现在长春。在长春饥饿的街头,只有狗最胖…我们也彻底消瘦了。皮肤苍白,血管暴露,眼睛塌陷,鼻子变尖,只有肚子鼓得很大。由于缺乏维生素,皮肤开始溃烂,肉也开始溃烂。头发上有溃疡,所以没那么疼。很痒,所以不小心摸到手指破溃处,然后一厘米见方左右的头发,连头皮都被拔掉了。长春市被完全断粮后,因饥饿而死的人纷纷出现,饿死者大多是无辜的老百姓,其中就有我的哥哥和弟弟。”9月,戴孝的父亲为了不让家里任何人饿死,决定设法逃离长春。然而,长春市内外都被双层铁丝网包围着。夹子是指夹在这两层铁丝网中间的区域。这家人钻穿了里面的铁丝网门后,外面的门被封闭了。“我问爸爸,那个门不开吗?”“它打不开门!”爸爸说。在国民党和八路军的中间地带,去往解放区的出口方向,栅栏门被严密地锁着。旁边一个中年日本女子说:“那个门是一周开一次,甚至一个月才开一次。四、五天前才刚开过……”年仅七岁的戴孝被困在这个中间地带,睡在成堆的尸体上,甚至目睹难民中的中国人吃死人。“在这个人类聚居区的可怕环境中,我失去了记忆。”10. 所有“故事”的后续,一纸苍凉我站在70年后的出口处,梳理着所有故事的“结局”,这的确是世界上最荒凉的经历——在这些记录的背后,还有更难以形容的事件中的消失和湮灭。文章开头民国三十七年那张照片上的逃难人家,一路风餐露宿,当年滞留四平街。第二年开春,锦州、沈阳已解放,火车开通了,继续上路奔河北乐亭老家。“我妈到家以后,死了,穿的那身装老衣服,从农安带了一路,有思想准备,原本想死在哪就埋在哪……”王洪志平静的说。来自四平的难民潘玉兰逃出重围,嫁给了一个男人,定居在公主岭的范家屯。“我十四岁来到这里,我的亲戚人口众多。十五岁时,我找到了我丈夫的家庭。那是一口袋高粱,一个扁平的盒子...还有这个手镯。60多年来,这个扁平的盒子已经分崩离析,手镯仍然戴着。”人生就像一眨眼的功夫,到处都是儿孙满堂。吉林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周励女士,认真的在她的一本书上为我签名,《回望故土——寻找司马桑敦》,她说,这本书献给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父亲,“父亲离开长春后,在台湾《联合报》任职二十几年,尽管这一社会关系,给我们姐妹带来不少灾难,但内心深处……始终企盼能有见着父亲的那一天。当两岸可以沟通交流,我刚刚找到父亲,还没来得及述说离情,他却突然离世了。”如果说,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可以弥补,那就是自己的母亲,“周墨萤女士,有个回忆录,很长,是录音,磁带,我正在整理。”卞,卞家大院的学生,在天津经历了解放战争。同一时期,发生了太平轮事件。他说他差点去了台湾省。后来因为年纪小,思念母亲,1949年初回到长春。"...这边家大院,终于剩下这个东西了。发条,一百年了,但是污泥太大了,擦不动。如果出了问题,没有人会去解决。”国立长春大学的新生孙景春,一天课都没上,就在历史的转角转换了身份:“出卡子后,有个叫刘家屯的地方,有解放军的接待站。再走,前后都有解放军跟着,背着枪。之后绕道奔九台方向,奔吉林。吉林八百垄,东北大学大石头楼,我们手拿着国民党时的高中毕业证、大学录取通知书,去登记,报道,编班。先学习政治,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2017年7月26日,台湾省李红将军的妻子马一真“在睡梦中安详辞世”,享年95岁。那位滞留东北的日本移民,小代,出围城后,经由吉林、延吉、天津,辗转五年的漫长光景,终于在1953年9月,“站在了驶向日本的船的甲板上”。2018年6月,我在电子邮件中问这位老人,是否还记得1948年在长春的住处,我想去看看。“真高兴你没有忘掉我,也知道了有读者关心我的故事。衷心感谢!我找过。不过我住过的房子已经被拆掉了。西安大路423号。是现在的香格里拉饭店的斜对面。”70年前,当我们还在为温饱和生存而打内战的时候,更文明的地方已经在讨论是否要违心招募士兵,是否要绑架更多的人参战,甚至失去生命。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1980年,普利策新闻奖将特别奖颁给了《奇普的最后一站》:一战老兵爱德华·奇普为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安排了一次长途火车旅行,前往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接受了军事记录修正委员会的听证,只为将自己的“一般退休”修正为“荣誉退休”——一种“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的维护。2018年,韩国大法院宣判血战钢锯岭无罪。为曾经发生的历史哀悼、反思、抗战、珍惜和平,哪怕竖起一块小小的石碑,爬山越岭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小标题下的括号是面试时间和地点。② 文中人物除注明外,全部实名;文中口述史部分,均有录音对照。“等待银行结束战争”是指1948年10月21日,守城首领郑洞国放下武器走出银行大楼,围城战全部结束。▍大赛组委会组织者:这个网站联合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今日头条指导单位:上海市作家协会学术支持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与传播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深圳大学传播学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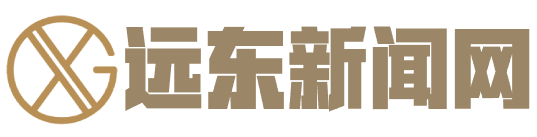
 新闻快讯
新闻快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