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朽 暗夜里的腐朽、蒙昧与晨星: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世界
导语:随着15世纪的过去,历史进入了16世纪。旧世界似乎正伴随着新世界的到来而逝去: 罗马帝国的余脉拜占庭帝国业已崩溃;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白尼的日心说颠倒了整个宇宙;路德重新塑造了基督教。一切旧世界
随着15世纪的过去,历史进入了16世纪。旧世界似乎正伴随着新世界的到来而逝去: 罗马帝国的余脉拜占庭帝国业已崩溃;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哥白尼的日心说颠倒了整个宇宙;路德重新塑造了基督教。一切旧世界的根基曾经看起来是何等稳固,而今在变革的风暴中都崩溃了,为一个迥异的新时代的到来扫清了道路。今天回顾过去,我们很难想象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子。当人们看到“中世纪”这个词时,会想到一幅黑暗的哥特式图画,画中充满了躲避世界的僧侣和迷信叛逆的农民。对现代人来说,一切似乎都很奇怪。我们是彻头彻尾的民主平等主义者,但中世纪的人认为一切都是等级森严的;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如何培养自己,如何养活自己,如何放纵自己,而中世纪的人却极力否定或贬低自己。比较永无止境。但这是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这是为了理解当时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神学语境。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作为一场革命,它在为某个目标而战,也在为某件事而战,而宗教改革所抵制的是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那么,在宗教改革前的两个世纪里,做一名基督徒是什么感觉?教宗、神父和炼狱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所有道路都通向罗马,这并不奇怪。耶稣曾经对使徒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据说就是这个彼得死在罗马,葬在罗马,教堂就建在他身上。因此,正如罗马帝国以罗马为母,以凯撒为父。时至今日,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帝国仍然以罗马教会为母,以彼得的继承者为父,“父”或“教皇”。与此略有不同的是,让罗马尴尬的是11世纪从罗马教会分裂出来的东正教。然而,每个家庭都有害群之马,其他基督徒把罗马和教皇视为不可替代的父母。没有教皇作为父亲,就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作为母亲,就没有救赎。围绕教皇的游行队伍排成一行
教宗被奉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作为代理人,他就是上帝的一切恩典涌流下来的管道。他有权力按立主教,主教也有权力按立神父。只有这些神职人员才有权柄开启恩典的水龙头。那些恩典的水龙头就是七件圣事:洗礼圣事、坚振圣事、圣体圣事、忏悔圣事、婚配圣事、授职圣事和临终圣事。首先,人们通过接受洗礼的神圣事物而被接纳进入教会,然后开始品尝上帝的恩典。然而,圣餐是整个体系的真正核心。只要走进当地的天主教堂,你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教堂里,所有的建筑设计都面向祭坛,这是举行弥撒的地方。它被称为祭坛,因为基督的身体将在弥撒中再次献给上帝。日复一日,牧师向上帝献上这种“不流血”的牺牲,重复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的“血腥”牺牲,从而平息了上帝对罪恶的猛烈愤怒。每天基督都作为赎罪祭献给上帝。这样,每天的罪都被处理了。 然而,这个献祭过程有所欠缺,基督的身体并没有在祭坛上,神父手拿的不过是饼和酒而已,这一点不是很明显吗?这正是变体说教义的过人之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个事物都有其“本质”,也有其“偶性”。比如说,椅子的“本质”可以是木头,但其“偶性”就可能是褐色或肮脏。给这把椅子刷一下漆,它的“偶性”就会改变。变体说所想象的正好相反: 饼和酒的质地在弥撒中被转化成基督真实的身体和血,而饼和酒原来的“偶性”未变。这一切看上去那么不着边际,然而有许多故事在天主教各教区流传,足以说服有疑惑的人。这些故事说某人看到了圣餐杯里有真正的血,或餐盘里有真正的肉等等。一旦牧师用拉丁语说出基督的话,变革的时刻就会到来。然后,教堂的钟声响起,牧师举起了蛋糕。普通信徒一年只能吃一次这个蛋糕,所以他们只需要看着被举起的蛋糕,恩典就会降临到他们身上。因此,有更多虔诚的人从一个教堂冲到另一个教堂,只是为了看更多的弥撒,获得更多的恩典,这并不奇怪。 支撑整个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体系和思想的是一种可追溯至奥古斯丁的救恩论。准确说来,就是奥古斯丁的爱的神学。奥古斯丁教导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爱上帝。然而,我们凭本性却做不到,必须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上帝凭“让我们称义”帮助了我们,而按照奥古斯丁的说法,“让我们称义”就是上帝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恩典的果效,而恩典据说是上帝通过这些圣事倾倒给我们的:上帝通过让我们更有爱心、更公正来“让我们称义”。据此而论,上帝的恩典就是让一个人变得更好、更公正、更公义、更有爱心所需要的燃料;而这种人至终就应获得拯救。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凭恩典得救。上帝把他的恩典倾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更有爱心,因此值得得救。奥古斯丁的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棒。但几个世纪后,这种思想逐渐蒙上了一层黑暗的色彩。中世纪的神学家以愉快和乐观的语气谈论上帝的恩典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的口号令人振奋:“上帝不会拒绝给那些尽力而为的人恩典。”但是你怎么能确定你已经尽力了呢?你怎么能确定你就是那个值得被拯救的人? 当然,教会的官方教导清楚指出,没有人在死的时候,有足够的公义让他配得救恩。基督徒若不是犯了致死的罪,比如杀人罪,而且没有悔改,那么他在死后还是会有机会,即他的罪会在炼狱中被慢慢地洗除净尽,然后他就洁净了,就可进入天国了。大约在15世纪末期,热那亚的凯瑟琳写了《论炼狱》一书。她在书中生动地描写了炼狱。她解释说,灵魂在那里渴望被洗洁、被净化,直到合乎上帝的要求,因而能够欣然接受惩罚。然而,那些比凯瑟琳更属世的灵魂,一想到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惩罚,就没那么愉快了。大多数人面对此种前景,没有任何喜乐可言,他们只想很快走完炼狱中的旅程,也想要他们所爱的人很快走过。他们为在炼狱中的人祈祷,也为他们做弥撒,相信上帝通过弥撒倾倒下来的恩典,可直接应用于已经去世或在炼狱中受刑罚的灵魂身上。于是,一整套因炼狱的教导而出现的产业发展起来: 有钱人设立小教堂,请神父专门在里面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幸运受益人祈祷和做弥撒;不那么有钱的人也为着同样的目的联合起来,形成互助会,共同出钱请神父。炼狱中的惩罚
中世纪天主教的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圣徒崇拜。欧洲各地到处是圣徒留下的圣迹。这些圣迹之所以重要,不仅有属灵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圣迹往往有圣徒留下的足够多的遗物,这就保证有人源源不断地前来朝圣。这样一来,谁都不吃亏: 朝圣客瞻仰了圣徒遗物,在圣迹收税的人也有了丰厚的收入。在整个中世纪,基督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变得越来越让人望而却步,这种状况似乎让圣徒崇拜兴盛起来,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复活升天的基督越来越被看作世界末日的审判者,全然圣洁可畏。谁能来到他面前呢?他肯定会听他母亲的话。于是,当基督退到天上去时,马利亚成了人们赖以接近他的中间人。然而,马利亚也被赋予了很多荣耀,她转而又成了天上的女王,光芒四射,令人无法靠近。照此逻辑,人们又开始向马利亚的母亲安妮祈求,让她向马利亚代求。于是圣安妮崇拜兴起了,吸引了很多人热心敬奉,其中包括籍籍无名的德国人路德一家。不只是圣安妮,天上满是圣徒,都很适合作罪人和审判者之间的中间人。而地上似乎到处都是他们留下的遗物,这些遗物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恩典和功德带给人的物件。当然,有些遗物是否真实,颇令人怀疑。有一个笑话说,在基督教世界的各处有太多“真十字架的残片”,要是加在一起,原来的十字架可就太庞大了,没有人能背得动。但基督能背得动,他毕竟是全能的。玛丽和圣徒受到尊重,而不是崇拜。这是当时天主教会的官方声明。然而,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大众来说,这种说法相当难以捉摸。更多的时候,整群圣人被当作万神殿,他们的遗物成为辟邪的神奇物件。如此复杂的神学体系,如何传授给不识字的人,让他们避免拜偶像?现成的解决办法是这样的:即使在最简陋的教堂里,人们也在圣徒和圣母玛利亚的图画和图像之中。这些图像要么是玻璃画、雕像,要么是壁画。这是穷人的圣经,文盲的书卷。既然文字不能用,人们就从图像中学习知识。但是,这个说法有点空的漏洞。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很难教会人们区分尊重和崇拜。此外,天主教会用拉丁语做礼拜,大多数人不懂拉丁语。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教民并不是天主教的优先事项。一些神学家想绕过这一点。他们认为拉丁语是一种神圣的语言,因此它足以影响不懂拉丁语的人。听起来不太可能。事实上,在他们看来,人们不需要理解,就可以接受上帝的恩典。一个未成形的“沉默的信仰”就足以让他们接受上帝的恩典。的确,因为缺乏指导,只能这样。玛丽和天后阿尔布雷特·丢勒在1511年制作了木刻版画
改革前夜,基督教是朝气蓬勃,还是腐败透顶?如果你运气不好,发现自己和一群研究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在一个房间里,如果你想活跃气氛,不妨大声抛出这个问题:“改革前夕,基督教是充满活力还是腐败?”我保证你会挑起一场大战。几年前,这个问题几乎被忽略了。当时大家都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皈依之前,欧洲人在痛苦中叹息,期待改变。他们痛恨腐败的罗马教会强加给他们的沉重枷锁。这种观点现在站不住脚。 历史研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历史研究,毫无疑义地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时代,宗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流行。当然,有人发牢骚也是免不了的,但绝大多数人显然怀着极大的热情委身宗教。与从前相比,更多人花钱为去世的人做弥撒,更多的教堂被建起来,更多的圣徒雕像被树立起来,更多人去朝圣。属灵书籍在有能力阅读的人中间也格外流行,在这类书籍中,有关敬虔和灵修的内容彼此掺杂在一起,就像现今一样。人们有宗教热情,这意味着他们渴望改革。在整个14世纪,每一个秩序都在改革自己,甚至教皇也经历了零星的改革努力。大家一致认为天主教堂的树上有一些枯枝和一些烂苹果。在《神曲》中,诗人但丁把教皇尼古拉斯三世和博尼法斯八世放在了地狱的第八层。当人们读它时,他们经常隐藏他们的音量并大笑。当然,也有老教皇和牧师过着腐败的生活,在弥撒前喝醉。但人们还能笑的事实说明教会是多么的稳定和安全,似乎教会还能承受这样的话语和笑声。他们想砍掉枯枝,这说明他们有多爱这棵树。他们如此渴望改革,以至于根本无法想象。也许后备箱里有致命的腐烂。毕竟,想要一个更好的教皇和根本不想要教皇是两回事;想要更好的牧师和弥撒与不想要牧师的职位和弥撒是不同的。但丁不仅在《神曲》中惩罚了坏教皇,还定制了上帝对反对教皇的人的报应,因为教皇,无论好坏,都是基督的代理人。宗教改革前夕,大多数基督徒都是这样:他们献身于宗教,致力于改进宗教,但他们不想推翻宗教。当时,社会希望看到的是清除常见的错误,而不是彻底的改变。这样看来,当时的基督教是朝气蓬勃的,还是腐败透顶的?这是错误的对立说法。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基督教无疑受人欢迎,并且充满活力。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健康的,或合乎圣经。实际上,如果所有人所渴望的正是宗教改革即将带来的那种变革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宗教改革只不过是一场顺其自然的社会运动,是一场道德上的清理而已。改教家们一直以来否认这一点。那不是一场道德层面的改革,而是直指基督教核心的挑战。他们声称上帝之道闯入了这个世界,并要改变这个世界。这场改革出乎时人预料,也与他们的想法格格不入。那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发事件。分裂宗教力量 宗教改革或许不是当时人们所期望的,大多数人只满足于小范围的改革。然而在中世纪的晴朗天空中,黑云开始出现。一开始只是巴掌那么大,没人在意,但那却是预兆,预示着天穹即将塌陷,砸向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第一朵云出现在罗马。1305年,波尔多大主教被选为教皇,但他以各种理由拒绝移居罗马。当时,人们期望教皇住在罗马,但大主教选择将教皇的总部设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法国国王得知教皇是法国人,住在法国非常高兴,这对于做事来说非常方便。然后,如果当选的下一任教皇也是法国人,他选择住在阿维尼翁,没有人会感到惊讶。事实上,接下来的几个教门真的是这样。法国以外的人就没那么兴奋了。相反,他们称这种情况为“流放中的巴比伦”。教皇应该是罗马的主教,罗马教会是所有教会之母。然而,这些住在阿维尼翁的人真的是罗马的主教吗?就这样,基督教社区开始对教皇失去信任。 七十年以后,罗马人再也忍无可忍了。教廷毕竟曾是罗马的尊严的最大来源。于是,当1378年枢机主教团正在罗马开会准备选举下一任教宗时,民众把他们包围起来,要求他们选出一位合适的意大利人来作教宗,而且最好是罗马人。受惊吓的枢机主教们让步了。然而,选出的新任教宗刚愎自用,争强好胜,枢机主教们见此后悔莫及。许多人说这场选举结果无效,因为它是在受人胁迫之下达成的。于是他们又选出了另一位教宗,仍然是法国人。可先前选出的那一位教宗身体状况良好,他拒绝逊位。这样就出现了两位教宗,彼此自然要把对方逐出教会。结果出现了两个神圣父亲,这就需要有两个母教会。整个欧洲在教皇支持哪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法国当然支持法国教皇,而英国本能地支持另一个。这种情况不能持续太久,所以相关人员召集了一次公开会议,希望能结束混乱局面。这次会议达成的解决方案是罢免两位现任教皇,同时选举一位新教皇。然而,让两位教皇退位并不容易。结果,出现了三位教皇。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分裂”。伟大的分裂后来被更强大的康斯坦茨国会解决了。康斯坦茨会议从1414年持续到1418年。会议成功地让三位教皇中的两位同意辞职,而住在阿维尼翁的第三位教皇拒绝辞职。于是会议宣布他被免职,并选举了一位新的教皇来取代之前的三位教皇。除了少数人仍然支持阿维尼翁教皇外,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新教皇。分裂结束了,但却引发了权威危机:教会的最高权威在哪里?在阿维尼翁还是罗马?既然公开会议已经确定了哪一位教皇是唯一合法的教皇,那么公开会议是否拥有比教皇更高的权威呢?分裂局面结束后,权威危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康斯坦茨议会宣称议会的权威高于教皇,但随后的几个教会拼命反对这种说法。这么多人互相争斗,普通基督徒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 同时,有好几任教宗住到别处,罗马城因而日渐衰败了。这是羞辱,但还不只是羞辱。罗马若是基督教界各处所仰望的荣耀的母亲,她就不会成为破败之城。若要恢复她昔日的地位,就需要让她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荣耀,要让整个欧洲都为之赞叹。在此后的一个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历任教宗把一大批璀璨明星都拉进了他们的轨道: 弗拉·安杰利科、戈佐利和品杜里秋都曾接受过教宗聘任;拉斐尔被委任来梵蒂冈修饰教宗的私人宅邸;米开朗基罗来修饰西斯廷教堂;布拉曼特来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切辉煌盖世,但花费之高令人咋舌。教宗到处筹款,百姓开始抱怨,说教宗似乎对他们的钱袋子比对他们的灵魂更感兴趣,又说那些艺术类玩意儿看上去更像是异教的东西,而不像是基督教艺术。重修圣彼得大教堂所带来的恶果,远超过教宗最可怕的噩梦,因为它将激发马丁·路德的怒火。 此外,罗马城开始弥漫腐烂的气息,加上表面的浮华,俨然就是那个时代的拉斯维加斯。尤其是在博尔贾家族统治下更是如此。1492年,罗德里戈·博尔贾只采取了简单有效的一步,就收买了足够的选票,被选为教宗亚历山大六世。于是,一段让枢机主教们难堪的教宗执政岁月就此开始了。新教宗有多个情妇,为他生了许多孩子。据说,他还和他的一个热衷举办宴会、戴毒戒指的女儿卢克蕾齐亚生了一个孩子。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习惯于在梵蒂冈举办宴会,并且毒杀枢机主教。他的所作所为没有给神圣父亲这一职分树立一个好榜样: 他的继任者好战的尤利乌斯二世在诸多方面也是前任的那种“爸爸”。尤利乌斯的继任者利奥十世则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然,教宗职分此前也曾有过低谷,但当教会处在权柄危机中时,失去人们的敬重实在糟糕。此外,罗马开始有腐烂的味道,表面浮华,就像那个时代的拉斯维加斯。尤其是在波吉亚家族的统治下。1492年,罗德里戈·波吉亚采取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步骤,赢得了足够的选票,当选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是,一段令红衣主教尴尬的教皇执政时期开始了。新教皇有很多情妇,为他生了很多孩子。据说他还和女儿Lucrezia生了一个孩子,女儿热衷于举办宴会,戴着毒戒指。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习惯于在梵蒂冈举办宴会,毒害枢机主教。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为圣父的位置树立一个好榜样:他的继任者,好战的朱利叶斯二世,在很多方面也是他前任的“父亲”。朱利叶斯的继任者利奥十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当然,教皇的地位之前有过低谷,但当教会处于权力危机时,失去人们的尊重真的很糟糕。
1493年的罗马
伊拉斯谟与古腾堡印刷术阿维尼翁空上形成了另一片云。它的出现可能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但它似乎是最无辜的云。和住在那里的教皇关系不大。这是因为阿维尼翁住着一个叫彼得拉克的年轻人。在那里,他不仅成长为一名诗人,而且成为了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古典文学学者。到了20世纪30年代,彼得拉克开始相信历史由两个阶段组成:一个是古典文明和文化的辉煌时代,另一个是他所谓的无知和野蛮的“黑暗时代”。在他看来,“黑暗时代”始于罗马帝国衰落的5世纪,一直持续到他那个时代。然而,彼得拉克也梦想着未来的第三个时代,那时古典文明将会再生。彼得拉克
彼特拉克有一班追随者,他们开始被称作“人文主义者”。他们期待古典文化的再生,并因此兴奋不已。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终结这个“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他们以优美的古典文学和文化为武器,来围攻他们那个时代的无知。而“回到源头!”就是他们的战斗口号。这种状况对于教宗统治的罗马来说相当不幸,因为罗马教会正是在中世纪的黑暗中成长起来的,而新学的光芒绝不会对她客气。罗马教皇的权力主要靠君士坦丁的恩赐支撑。据说这份文件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4世纪写给教皇的。上面说,当君士坦丁把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时,他给了教皇统治罗马帝国西半部的权利。中世纪教皇声称他们对欧洲拥有政治主权,这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教皇高于国王。然而,当一位名叫洛伦佐·瓦拉的人文主义者对这份文献进行考证时,发现它实际上是在8世纪用拉丁语写的,而不是在4世纪,而且是8世纪的写作风格。这份文件是伪造的。1440年,瓦拉公开了他发现的秘密。这相当于摧毁了教皇一项重要声明的基础。不仅如此,还让人怀疑教皇的所有说法——还有哪些传统信条可能是伪造的? 瓦拉最伟大的遗产还是他所着的《新约注释》。这本书是把他生前未曾出版的笔记搜集起来编纂而成。从这些笔记可以看出他受过很好的希腊文训练,他借此指出天主教会的官方武加大译本存在错误。但由于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笔记并未出版,因而他从未看到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瓦拉死后,新一代人文主义者出现了,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发现了瓦拉留下的笔记手稿,将其编辑出版,并进而使用它们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成为反击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最有力的武器。1516年,伊拉斯谟回归信仰之源《圣经》,出版了希腊文版《新约》。除了希腊文,他还列出了拉丁文译本,但他列出的不是天主教的官方译本,而是他自己翻译的经文。伊拉斯谟的目的是敦促教会做出一些道德上的改进。然而,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希腊新约会给罗马带来伤害。事实上,他当时甚至把这本新约献给了教皇,教皇回信表示感谢,并提出了很大的建议。但是教皇的回答为时过早。因为每当伊拉斯谟的《新约》与官方版本的《乌加》不同时,都会涉及到神学上的差异。例如,在马太福音4: 17中,耶稣的话被翻译成“...“由吴嘉达赔罪,并”...由伊拉斯谟的《忏悔》,再翻译成《改变你的想法》。如果伊拉斯谟是正确的,那么耶稣实际上并没有像罗马天主教那样教导人们进行外部赎罪,而是说罪人需要在内部改变思想,远离罪恶。如果罗马天主教会曲解了这段经文,她还曲解了什么?她有什么精神权威?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是一颗定时炸弹。德西德里奥·伊拉斯谟
人文主义者的学术活动挑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与此同时,他们追随彼特拉克,倾向于批判当时的神学家。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看来,神学家似乎只对那些最晦涩和无关痛痒的问题感兴趣。比如:“有多少天使可以在针尖上跳舞?”或者“上帝能否变成黄瓜,而不是变成人?”邓·司各脱被认为是这种思维方式“微妙”的神学家的代表,在当时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他简直就是蠢人的典型。凡是追随他的人也都被嘲笑为“邓人”或“蠢材”。神学家成为人文主义者所写讽刺文学的主角。1513年,朱利叶斯二世去世,第二年,一本名为《朱利叶斯停在天堂门口》的小册子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伊拉斯谟从未承认这本小册子是他写的,但我们手边有一本这本小册子,上面的字迹是伊拉斯谟的,这证实了大家的猜测。根据这本小册子的描述,朱利叶斯像往常一样穿着衣服,戴着头盔,留着标志性的胡子,来到天堂门口,这是他发誓要为许多敌人报仇的证据。他知道他可能会遇到障碍,他带了一个魁梧的保镖,如果有必要,他可以砸碎大门。然后,看门人彼得让朱利叶斯看起来又蠢又自负,然后故事的结尾就由标题预先指明了。最终,教堂和神学家成了人文主义者的笑话,这算不了什么。这个笑话清楚地表明了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寻求真理的不同路径已经开始挑战教会的权威:学者会比教皇更了解真理吗?罗马和她的神学家错了吗?古腾堡印刷机
如果这些人文主义者的学识只留在象牙塔里,那他们搅动起的争议倒也无关紧要。但技术的发展却似乎与他们一拍即合。1450年前后,古腾堡发明了第一台印刷机。到了15世纪80年代,印刷所在欧洲各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时候,书籍可以很快被成批印制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知识的传播更快了。印刷出来的第一本书就是古腾堡拉丁文圣经,这一点意义非凡:真道广传的时代已然来临。本文摘录自《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里夫斯 着,孙岱君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3月。本站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免责申明:以上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不代表远东新闻网立场!登载此文只为提供信息参考,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目的。如有侵权或内容不符,请联系我们处理,谢谢合作!
当前文章地址:https://www.ydj6688.com/tiyu/438755.html 感谢你把文章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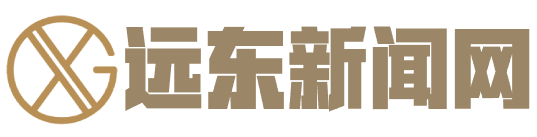
 体育新闻
体育新闻